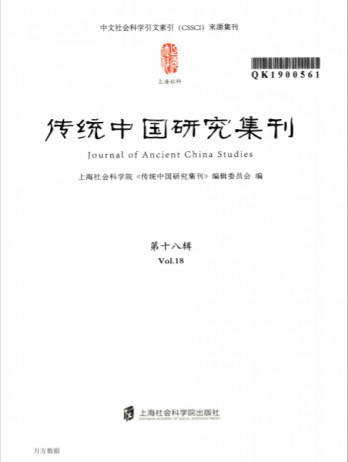传统绘画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9-16 04:43:31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传统绘画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60年代后。港台地区逐渐开始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等国学者的画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一些重要论著,几乎均有出版,有的甚至后来还被多次再版发行。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将黄宾虹、邓实编选的《美术丛书》1947年全四集增订本影印出版,同时,又有《百部丛书集成》的编者严一萍加入,将《美术丛书》增加至五集,1975年又增加至六集。1967年9月,台湾中华书局对余绍宋的《画法要录》初编二编分别以精装2册和平装4册的形式做了影印发行。1980年11月。又以平装二册的形式再版。进入70年代后,像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著作又先后受到重视。1972年,台北京华书局将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影印出版,1982年又再次发行:而1975年,华正书局也分别于1975年和1984年影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画论类编》。至于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则分别有台湾世界书局1974年和1984年影印本。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翻印出版,风行东南亚各国,1984年,台湾华正书局也翻印出版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两卷本)。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陈传席的《六朝画论研究》。
与大陆不同的是,港台地区的艺术史论学者,多半都有留学或游学欧美的经历,因此,译介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不仅增强了彼此间学术联系,也是对学界学术视野的拓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绘画理论研究。这里姑且择其要而述之。1982年。台湾学者姜一涵、张鸿翼选译卜寿珊《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书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并以《北宋文人的绘画观》为题发表于《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1卷2期:1988年。童元方翻译了卜寿珊的《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的途径兼论诗与画的关系》,登载于香港《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4年,张保琪翻译了高居翰的《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发表于《美术史论丛刊》总第11期。
二、港台地区的古代画论研究
与日本、欧美等国及大陆地区一样,中国港台地区的画论研究者多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像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都扮演了重要的研究角色。
1.台湾的画论研究
(1)溥儒《寒玉堂画论》《论画》
被誉为“渡海三杰”之一的画家溥儒(1896-1963)赴台后,曾著有《寒玉堂画论》和《论画》二书。溥儒出身皇族,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基础,工诗文,精书画,又曾饱览宫内旧藏书画,无论其创作还是绘画思想,都对传统体悟甚深。根据他在《寒玉堂画论》一书前的自序可知此书写于1952年9月,所论多为具体的绘画技法问题,但溥儒行文时,常喜引经据典,观点也多沿袭古人,谢巍称其“文字古奥玄虚,乃借论画发挥”。“论用笔”和“论敷色”两篇。则有独到之见解,体现了溥儒个人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根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所述,《寒玉堂画论》最初发表于1956年6B台北刊行的《学术季刊》。1966年,安国钧编选的《寒玉堂画集》由台湾中央书局影印出版,该书除了选录“溥心畲遗作展”(台中图书馆1964年举办)中40幅精品外,还在书后附有《寒玉堂画论》。1975年,学海出版社辑印《寒玉堂画论》一书。书后附有溥心畲授徒画稿十四种,原为其门人胡文琮珍藏。
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溥儒的手写本《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752页),书中收录《论书》《论画》和《获麟解》三文。《论画》一文写于《寒玉堂论画》之后,即1957年中秋,系“经数年深思熟虑而作,乃其绘画理论之精蕴”。文中对于传神、写意、气韵、笔墨、设色等均有所阐发,更似为阐述画理之作。1974年,世界书局又进行了再版。
199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诗集》,书中不仅收录其诗作。还将《寒玉堂画论》和《寒玉堂书法论》列入其中。而《寒玉堂书法论》。包括“论书体流变”和“论书画相通”两篇。实为《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中的“论书”和“论画”二文。
(2)庄申《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
1959年6月。台湾中正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史研究》一书,全书收录了庄申撰写的13篇画史研究论文,其中《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一文,后被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收录。通过剖析董其昌、莫是龙的“南北宗论”的理论缺陷,继而提出了对中国山水画的新的分宗法,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可以分为李派、院派、唐宗派和元明派。其中,元明派自“四王”以后“遂分为虞山、娄东二大派,前者宗王原祁,后者宗王晕。其势至今仍胜于前述三派(指李派、院派、唐宗派)”。
(3)徐复观《中国艺术的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在台湾地区,最享誉海内外的成果当属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的精神》。这部由台湾中央书局1966年首次刊行的著作共有十章,除了前两章论述孔子、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外,另外八章均是关于古代画论的探试他认为:“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他还说:“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这一观点,固然失之偏颇,却也体现了它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于历代画论的解读,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给人无限启发。此书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迭经多次再版重印。而在大陆地区,则分别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三种。
1968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了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一书,他从对“一画”的解释入手,在阐释石涛画论的同时,也批驳了以往一些有关石涛画论的错误观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石涛的生年以及其晚年弃僧入道的问题,此书堪称石涛研究的专论。1973年,台北学生书局又出了此书的增补版。在将原书中《石涛简谱》删掉的同时。又加上了《石涛与问题》。
(4)姜一涵《石涛画语录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海内外学者对石涛及其《画语录》均给予更多关注的时期。或许是受学界这一研究风向的影响,1964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姜一涵(Chiang I-Han)完成了硕士论文《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其后,他对于石涛的《画语录》用力颇勤,在台湾《艺坛杂志》连续发表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续一至续十三)、《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后记――怎样阅读画语录》等系列论文。1981年10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其结集出版,书名为《石涛画语录研究》。1982年8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该书再版发行。在再版“序”中,姜一涵对这些研究中存在的得与失做了检讨。
(5)高木森的画论研究
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读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高木森(Arthur Mu-sen Kao,1942-),70年代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师从美国中国美术史泰斗李铸晋教授学习艺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1982年,他在《美术学报》16期上发表《论气韵生动》一文,在辨析中外学者对“气韵生动”释义的同时。认为“‘气韵生动’只是六法之一,也许比其他五法重要一点,但绝不是五法精备之后才出现的境界”。至于他所理解的“气韵生动”。则是“画家不论是画人像、动物或鬼神,若能表现丰厚的肉体,使之充满活泼的生命力。而且使肉体的举止高雅和谐。便得其法”。至于“气韵生动”的西文译法。他赞同艾威廉的译法,即“Reverberation of the life breath,that is,the creation of movement”,“这个译文译成中文便成‘生命气息之回响,也就是动的显像’。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略作修饰使之更近于谢氏原意‘the vital life breath and elegant movement’”。高木森的观点。角度新颖,有自己的创见。该文后被收入其名著《中国绘画思想史》第三章中。题目是《画论的启蒙――论气韵生动及其衍化》。而在这部由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高木森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画论的发展,阐述了从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绘画思想历程。1995年,高木森又在《美育》66期上发表“文人画理论之集大成――生熟巧拙争辨识,心性妙理费文章”一文,进一步显现了他对于明代后期绘画理论的兴趣。该文认为从嘉靖到万历时代,正是唯心画论高涨的时代,而“‘返璞归真’(回归真朴的本心――良知)正是此期画论的重心”。同时,这一时期的“画论有下列五大要点:唯心论、情趣论、生拙论、兴趣论和分宗论。皆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为下一世纪前五十年的人文思想和绘画奠定坚实的基础”。到了万历和天启时代,固然是画论家辈出,但是“这里出现的有趣现象是人们一方面要为文人画建立正统地位,一方面要加速文人画的分化”。该文后来则被收入其另一部著作《明山净水:明画思想探微》中。本书着重探讨了明代绘画思想的发展过程。
(6)白适铭的《历代名画记》研究
1995年。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白适铭(Pai Shih-Ming)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彦远的成书与士人绘画观之形成》,作者“循着《历代名画记》的记叙,联系唐代文化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探讨了滥觞于晚唐时期的‘士人绘画观’的形成过程、精神旨趣。并说明其理论架构”,而经过这一番探讨,作者认为。“张彦远作为士人阶层之一员,其所著《名画记》蕴含着新兴的‘士人绘画观’”。该文后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朵云》杂志“《历代名画记》研究”专集。1999年,白适铭又撰写了《那个时代:围绕于张彦远的政治・士人・著作三者之关系》(《s代名画记》とその时代:张彦远たぉける政治・士人・著作三者のがりふげべて)。该文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美学美衍史学研究室研究纪要》20号,体现出了作者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延续性和浓厚兴趣。
2.香港的画论研究
在香港地区,中国古代画论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其中,又尤以国学大师饶宗颐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讲座教授高美庆博士为最。
(1)饶宗颐的画论研究
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的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古代画论方面,虽然所撰写多为论文,但所涉及的均为画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到明清文人画。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到诗歌、词与画论的关联,他均有所涉猎。
在《札移》一文中,针对前人多注意《历代名画记》有关寺观壁画中人物、经变部分的记载,他则专注于其中关于山水的记载,“略举之,加以疏说,以补唐代画史之不及”,此文曾连载于1987年8月10日和19日的香港《大公报・艺林》版。在1986年所撰写的《张彦远论画分疏密二体》一文中。他提出“从张彦远的理论,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须从‘用笔’方面著力,这是中国画的特色”。而在其1988年所撰写的《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一文中。他认为“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在《诗画通义》中,他从“神思”、“图诗”、“气韵”、“禅关”、“度势”、“行恕钡确矫娣直鹇凼隽耸歌与绘画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原载于1973年八卷三期《故宫季刊》上的《词与画》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画和词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关系”。因此,“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曲子词和画的关联之突出的地方,画人如何运用词意以入画。画的原理与技法又如何被词人加以吸收作为批评的南针”。1975年,他又撰写了《方以智画论》一文,对于这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饶宗颐深刻地意识到了其绘画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以上若干见解。在明季画论中应有其独特重要性,不亚于董(其昌)、莫(是龙)之说。尚有待于抉发耳。”在《龚贤“墨气说”与董思白之关系》文中,他说:“有人认为半千这种强调黑白明暗的处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镂刻版画的影响,却很难说。”此外,他所撰写的《明季文人与绘画》《晚明画家与画论》等文也均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研究专论。充分体现了这位国学大师对于明清文人画、遗民画的真知灼见。成为从事艺术史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2)陈仁涛《金匮论画》
古钱币收藏陈仁涛(1906-1968)于1946年后移居香港,随即又开始了书画收藏,闲暇之余。著有《金匮论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书籍多种。特别是《金匿论画》(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版)一书,所收均为其鉴余随笔,包括论画宗南北、论院派、论文人画等文,特别是其中的“论画宗南北”一文,又被收入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一书。文中,陈仁涛在辨析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画宗南北之说,乃一时之激言,而非千古之定论,尤非玄宰持论之本旨。学者取其长而去其短以会其通可耳”。
(3)高美庆《石涛画语录探源》
篇(2)
雍正乾隆年间,画坛上的主要画家和绘画美学家有:四王、扬州八怪、唐岱等,师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思潮繁盛于时。这一时期具有审美作用的绘画受到皇室重视,宫廷绘画文人化现象明显,绘画风格多迎合达官贵人的审美趣味。画家主要以取法古人,取材自然为主导,创新意识不强,有拘于“师古”风习;“形神兼备”论受到热议,形与神都得到重视;以画抒情得到主张;绘画美学思想倾向于形式主义,并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张庚自幼孤贫,仅靠其母以针线活维持生计,有史载张庚“事祖母及母尽孝”,系钱氏近亲,少与钱维城、钱载共师从于南楼太夫人陈书画法,致力于经史、诗古文,十来岁为了生计开始历游各地,仍继续攻读诗书研习书画,后张庚与钱载萌茵于陈书的儿子钱陈群,同在1736年以博学鸿词科应荐入京。张庚在时代影响下,绘画注重“神”及意境,理论中有“师古自然”思想,以其历游各地的阅历,可见其“取法自然”,四处游学的踪迹。
张庚传世作品有乾隆十五年(1750)作的《仿江贯道秋林叠嶂图》(图录于《中国名画宝鉴》)和乾隆十九年(1754)作的《竹林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等。清・秦祖永云:“张庚逸品……笔意清洁雅秀,饶有韵致,惟姿颜媚弱,无古大家沈雄奇逸之趣,故秀润有余,苍浑不足……想是精于鉴赏。于笔墨一道,尚未深入古人也……所著论画,洞悉元微,足为后学取法。”秦祖永认为张庚的作品在品评中属于逸品,气韵雅致秀润,但不足之处在于苍劲浑厚不足。蒋泰评价为:“见居士画,若读逍遥游,祗见海、大鱼而已。”认为张庚的作品潇逸洒脱。
张庚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其绘画理论,著述有《浦山论画》又名《图画精意识画论》《国朝画征录》又名《翰苑分书画征录》和《图画精意识》等。
《浦山论画》约成书于1750年,论画八则分别为笔、墨、品格、气韵、性情、工夫、入门和取资。语言精短扼要,独抒心得,观点精到,可谓妙语连珠。总论中叙述了派别分类及简要起源,分别提到了南北宗、浙派、松江派、新安派、西江派、“闽派”等,列举了各派的弊病,并反映了张庚的绘画思想倾向。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中说:“张庚之《浦山论画》(美术丛书本名日《图画精意识画论》)是书亦仅有八则,首则为总论,论明初画派之弊,而仍推崇王原祁,亦师生关系使之然也,其余论笔墨品格气韵性情之功夫等,有推衍成说者,有独抒己见者,惟末一节论《取资》确为至理名言。
《国朝画征录》亦名《翰苑分书画征录》,三卷,又《明人附录》一卷,续编二卷。是出始撰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于雍正二十三年(1735),收入清初至乾隆年间画家466人,各为之评传。叙述其字号、生平、师承、画法特点、理论见解等。《国朝画征录》序中有言“读其所著画征录,其论宗法渊源造诣深浅皆确然有据而评骘不肯轻下一字非深于是者能乎。至若因人以及画或因画以及人另具奥旨微意有遗音矣盖深有得于史也。张庚“凡遇图画之可观者辄考其人而录之”,观点有据,评述相对客观,是一部断代史画史著作。张庚自述“凡画之为余寓目者”“征其迹而可信者,著于篇”。俞剑华先生评“张庚之《国朝画征录》一此书记张氏目所及见之画家,或一人一传,或数人合传,画家名言精论,亦多采入传内,传后论赞,亦极审慎,颇合史法;惟前后次序毫无规定,各种画派亦未分别,随手摘录,尚欠组织,至于推崇王原祁,贬抑吴历,尤欠平允。所列各家无特定规律可循,但从其评述中,可获知张庚的绘画美学思想及审美倾向。
《图画精意识》收录了张庚对部分画家的作品所作的评述,分析其笔墨之法,气韵之境等。王世襄在《中国画论研究》中说:“清代论画只著足与《玄览编》比拟者厥惟张浦山《图画精意识》一书。
在美术理论及绘画思想著述中多见引用张庚的理论观点,包括现今的学术论文、艺术研究等,足见其绘画思想的影响深远。
注释:
[1]《中国画学全史》郑午昌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P412.
[2]《清史列传》(卷七十一),P5870-5871.
[3]钱维城(1720-1772),清朝官吏、画家。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谥文敏。书法苏轼,初从陈书学画写意折枝花果,后学山水受董邦达指导,著有《茶山集》.
[4]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荐石,又号匏尊,晚号万松居士、百幅老人,浙江秀水人,清朝官吏、诗人、书画家。乾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库全书》总纂,山东学政。官至二品,而家道清贫,晚年卖画为生。工诗文精画,善水墨,尤工兰竹,著有《石斋诗文集》。钱载为乾嘉年间秀水诗派的代表诗人.
[5]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南楼老人,浙江秀水人。适海监钱纶光,以长子陈员责诏封太淑人。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其用笔类陈道复而道选过之。山水人物亦擅长,间绘观音、佛像等。后居贫卖画自给。著有《复庵吟稿》.
[6]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之下卷《书画名家》.
[7]《画史丛书(三)》.
[8]《中国绘画史》俞剑华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4第一版P243.
[9]同上.
[10]《中国画论研究》(伍)王世襄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P926.
新文人画要发展,不但是以复兴文人画为目的,更是要在继承文人画优良的传统上,大胆的弃其糟粕。传统的文人画家轻视画工,追求笔墨游戏,排斥其他流派的技法,一味模仿,过分强调传承,致使文人画走向了一个极端,影响了其自身发展。新文人画多了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并不简单,前辈们的技法娴熟,完美,需要继承,但在继承中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周慧.“新文人画”并非“文人画”.黑龙江:齐齐哈尔师专学报2006.
[2]杨仁恺中国书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徐书城宋代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薛永年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
[6]刘二刚几种选择北京:美术观察1997.11.
[7]陈绶祥新文人画艺术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篇(3)
关键词:龙脉;王原祁;开合;风水;中国古代绘画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2002年中贸圣佳会上拍卖了一件王原祁的作品《深壑溪庭图》(纸本设色立轴100×54cm),款识云:古人作画先定龙脉后,审起伏开阖总以气行于其间。画中行云流水皆舒气之法也。今人效颦每多为识者所诮。然精神工力非巨幅矣。无由施展。余故于子久一家苦心经营不自愧者未必匠心耳。质之具眼当必有以赐教也。康熙甲午九秋于谷治堂并题。王原祁七十有二。在王原祁的这段阐述中,可以感受到在其绘画创作中,给予“龙脉”以很高的位置,而在《雨窗漫笔》中,王原祁也曾主述过“龙脉”,他说:“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而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起伏由近及远,向背分明,有时高耸,有时平修,欹侧照应,山头、山腹、山足铢两悉称者,谓之用也。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M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且通幅有开合,分股中亦有开合;通幅中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过接映带间,制其有余,补其不足,使龙之斜正浑碎、隐现断续,活泼泼地于其中,方为真画。如能从此参透,则小块积成大块,焉有不致妙境者乎?”文献显示,在《雨窗漫笔》之前的清代画坛,很多文人画家论及绘画时经常选用风水用语,高秉的《指头画说》评及历代山水画,道:“唐宋元明诸家画法,皆以下为主,上为客,近主远客;在下近处作树石屋宇,在上处作峰峦沙岸;大家名家,皆不能逃此范围,至有阴起阳收之说,尖刻辈以作画亦讲风水诮之。”从对“尖刻之辈以作画亦讲风水诮之”一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时人对绘画与风水的纠葛实际上是有足够认识的,清初的笪重光的《画筌》主张:“分五行而辨体,峰势同形,谙于地理。”他认为山水画家应谙于“形势宗”的风水,其画论出现了“主山”、“客山”、“砂”、“水口”等风水用语。如:“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侧者客山远。众山拱伏,主山始尊;”等等,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风水与绘画的关联问题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费佛尔曾言:“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注:参见[法]费佛尔《为史学而战斗》,转引自何兆武等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在由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巨大潮流下,本文预设的问题是:王原祁《雨窗漫笔》使用风水术语“龙脉”一词的绘画史的意义又是如何?
一、“龙脉”一词的风水意味
甲骨文中,“龙”字常见的有八九种之多,龙,本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其长相,《广雅》描述道:“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易》、《诗经》、《书皋陶谟》、《左传》、《补三皇本纪》等都有龙的记载,《易经》中的乾为天卦提到“时乘六龙以御天”、“潜龙”、“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海”、“群龙元首”;坤为地卦提到“龙战于野”;震为雷卦提到“震为龙”。乾为天,坤为地;是天地间最根本的能量。东汉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龙”的解释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通常是被形容为神秘莫测的变化之物,而且见首不见尾,起伏顿跌、趋闪伸缩……。而“脉”,本义指血管,《说文解字》释“脉”作“血理分~行体者”,“脉”被视为流通血液的机体组织,象大地上的水流一样,纵横交错,遍布全身。风水家把山脉、河流的弯曲、转折、分敛、伸展等形象,以龙的变化莫测来比喻, 由于山脉在形态上与龙相似,风水学把山脉比喻做龙,把山脉的延绵走向称作“龙脉”,所以,龙脉最初是用于中国古代风水领域的。然而,就术词而言,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一方面,人文事实中的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语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有新的时解和新的使用背景介入,这种情况下,术语会存在着“转化”与“延伸”的现象,“龙脉”一词后来出现在王原祁的画论中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在清之前,风水与绘画就有渊源,在王微时代绘画曾被定位为“穷神变,测幽微”,“与易象同体”[注:参见[魏晋南北朝]王微著《画叙》。]的功能,《画叙》认为画不仅是图形,还有更深层的意味,可以象易一样推测自然和社会的的奥秘,且王微论及绘画之乐时,认为其之乐绝非“金石之乐,璋之琛”所能仿佛。及至北宋,郭熙认为“画亦有相法。李成子孙昌盛,其画山脚地面皆浑厚阔大,上秀而下丰,合有后之相也。”[注:参见[宋]郭熙著《林泉高致・山水训》。]沈子丞在《历代画论名著汇编》引述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所载郭熙逸事道:“熙虽以画自业,然能教子思,以儒学起家。熙喜其子思登科,乃于县痒宣圣殿内图山水窠石四壁,雄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所极得意于此笔矣!’后其子思既贵……。”天津大学的史箴认为:“郭熙此举,自然不只是喜庆,竭其平生本事,以相画之意,祈其子思亨通显贵,恐怕是更主要的动机。”[注:参见史箴《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兼析山水画缘起》一文,王其享编著《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除郭熙外,相信“画亦有相法”的文人画家,也不乏其人。如《辍耕录》引元代黄公望《写山水诀》:“李成画坡脚,须要数层,取其湿厚。米元章论李光丞有‘后代儿孙昌盛,’果出为官者最多。画亦有风水存焉。”[注:参见[元] 陶宗仪《辍耕录》。]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自然山水具有重要的堪舆学即风水学的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山水画的创作:山水画的拥有者希望画面山水具有吉祥之气;山水画的创作者也认为画面风水影响画家的命运;”[注:参见赵启斌《山水格局与龙脉气势》一文,《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所以,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创作中,受此文化背景影响的画家多少会有这样的潜意识:在经营位置中寻找最吉祥的表达,从这个角度看,寻找构图中的“龙脉”似乎是他们注定的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风水用语在王原祁时代时,与风水虽有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淡化了、减弱了,而更多的是从绘画作品本身出发,指向绘画作品中的气势及整体效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寻找最佳构图的努力。我们知道,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当语汇(术语的自然形态)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时,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最初是具有固定性和单一性的,但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语汇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随之变得模糊,同时语义也变模糊,经过历史演化,词源与引申意涵的关系已经不会局限于最初的语言体系内部,而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语境变化,所以,“术语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注: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文化十六讲》第16讲《中国近代术语的生成》,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对术语的研究可以作为考析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注:参见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从学术的大视野看,对术语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要在强调考察术语历史源头的同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的承袭、改造、转化、延伸等情况,这样看来,从语义的演变中可以捕捉到历史文化的变迁的轨迹。那么,考察“龙脉”这一概念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在绘画图式上的表达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王原祁对风水术语“龙脉”一词的修正
应该说,“龙脉”一词在绘画理论上的提出与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到一定阶段有联系,王原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艺文发展史最高的成熟阶段,种种可能的范例几乎已为前人所尝试,超越之难可以想象,而寻找突破历来是艺术创作首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点判断,当时寻求超越所引起的焦虑也是一种普遍的情绪,纪昀曾言此困惑:“后之人竭尽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范围。”[注:参见[清]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引纪昀语。]布鲁姆认为,“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会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之焦虑。试想,哪一位强者诗人希望识到:他并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注:参见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中译本,1989年版,第3页。]具体来讲,经董其昌对文人画的总结,“南宗正脉”,此时已尽善尽美,高度成熟,在笔墨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有所作为,而构图方面理论上的总结相比而言还欠缺,通过王原祁等人对布局形式感的探索,及画面上对古人丘壑的前移后挪的实际操作最终也达到了“经营位置”的烂熟阶段,所以艾尔金斯等人评价王原祁为中国画的形式主义的开山鼻祖,也是由一定的道理的,迈科尔苏立文(Michael Sulivan)在他的著作《东西方艺术的交流》(The Meering of Easrern and Western Art ,1989)中曾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立体主义者的目的和技巧早在中国画家王原祁(1642-171的山水画中已露端倪。这可能是因为王原祁和赛尚都采用了一种拆开山脉和岩石并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形成紧密有机团块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王原祁将董其昌“势”的主张发展为结合山脉走向的“龙脉说”,使之成为他画学思想中重要的关于山水画构图的理论,而之前的文人画家作品,除了笔墨的形式以外,也讲求画面的构成与经营,但形式始终不是文人画家追求的终极目的。这样看来,“龙脉“一词在王原祁画论中的出现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值得一提的是“龙脉”一词中的“龙”及与“龙”有关的概念是基于共同体认同所建构出来的具有绝对地位的“图腾”,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文化符号”,而且从古到今,“龙”及与“龙”有关的概念充分地行使了自身的符号资源,此文化符号,文化意识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地传统理念的根基中,朝代替换,但围绕着“龙”所延申出来的文化意义却牢固地镶嵌到了文字构造地文化血脉之中,甚至在无意识的层面施展着无声的霸权。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竟然没有出现超越其外的颠覆性替代方案,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符号权力”,使其具有了神圣吉祥意义的认同,其概念被提升到神通天地,礼序遍野的普遍性高度。所以与龙有关的含概应该是宏大而具有至正之气。从这点看,绘画领域中“龙脉”体也应该不会带有阴柔的气息。而且,王原祁的一生基本上沿着儒家嫡传体系运行的,受的教育是典型的儒家教育,王时敏也着力培养他,并于康熙九年中进士,和董其昌一样,他们的生命中曾有很大部分时间学习儒家的课程,儒家意识已经积淀在骨子里,我们知道,艺术需要以人的社会属性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的,在《麓台题画稿》他曾道:“六法一道,非惟习知之为难,……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简练以为揣摩,于清刚浩气中具有一种流丽斐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学大痴者宜深思之。”这种“清刚浩气”与康熙时期统治者推崇基于程朱理学的所谓方苞与姚鼐等桐城派文论及沈潜德一派诗论是相呼应的。
况且,“龙脉”一词与”气势”一词在绘画领域中也是很有关联的,王原祁认同董其昌的看法,认为一幅山水画最重要的是有“气势”,他还认为“龙脉”就是山水中的来龙去脉的气势所在处,从这个角度看,在绘画领域,清初“龙脉之说”与“画中气势”有意义叠和之处,绘画美学上“气势”开启了儒家美学的刚健一脉,与强调禅道意味倪瓒一脉有所区别,其他文艺领域有杜诗,韩文、颜字、辛词,它们在精神气质上都是偏重儒家的,以气势撼人,儒家礼乐之典《礼记・乐记》言:“乐者,乐也。”和谐之乐,不应该太过激荡,无论在董还是王的画中,都看不到希腊文化所推崇的“酒神精神”,因为这些在儒家意识看来都是感于物而动过了头,“是人欲的泛滥,既盲目又不澄明,而且自相鼓荡永无止歇,从根本上是反生命的,”[注:参见叶朗等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儒家文化的面貌不是阴柔的而具有爆发力的。但这正是“中和”的宇宙,社会和心理秩序被破坏以后,由挠、荡、激、梗、炙、击而后心灵所发,“其深层背景仍是要”致中和“,”致平“的,考虑到这一深层背景,所以儒家诗教的确强调在发不平之鸣时,也要注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否则过了头,就会乖于其”致中和“的深层背景,”[注:参见叶朗等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可以说,王原祁其作品也相应地比较“雅正”,他说:“作画以理,气,趣兼到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于平中求奇,绵囊有针,虚实相生,古来作家相见,彼此合法。稍无言外意,便云有伧夫气……,”“平中求奇”意味着他不会创作比较另类的作品,当然这里所说的另类是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
具体就画面而言,绘画也存在文本的开放性问题,它是此时代人的自由精神及理性精神所能臻达程度的一个标志,王原祁极推崇黄子久,在《麓台题画稿》53则中,仿子久的多至25幅。所谓的“子久”,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绘画符号,而是上升为一种绘画“传统”,是以“子久”为中心,上溯董、巨逸轨,旁及倪瓒王蒙并泛滥后世诸家的一个谱系系统,且被后世视为“南宗正脉”。身为道士的黄公望有“画亦有风水寸焉”的言论,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提出“龙脉”一词,但在绘画上却多少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它,其作品《富春山居图》即是经营位置的重要依据,也是“龙脉”表达的范例。李雪曼在《中国山水画》一书中认为:“对同时代的人来讲,黄公望作品中的理性成分多少有些向北宋大师作品回归的意味,但是事实上,解读此作品,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还是抽象因素而不是再现”[注:A detail of his famous Fu Ch’un Mountains handscroll may reveal something of the rational quality in brushwork and composition that seemed to his contemporaries a true return to the great masters of Northern Sung But it is in effect a new style with a more abstract ,less representational type of brush stroke,a purer and more remote air derived in large part from the judicious display of numerous and complex areas of white paper like the art of Poussin ,Huang's art seems "aesthetic",selfconscious in the best sense ,a style of painting for those wno love painting,including first and foremost ,others painters “ Sherman Elee : Icon Editions Harper &nRow ,Publishers page 45],与北宋较写实的山水相比,此图的确较为概括,但山水意象层次分明,接连起伏,状若蛟龙,灵动而随意,在微妙的虚实之间过渡得非常自然,黄公望深谙气势或龙脉之理,把握住画面全局大势,以随意而游走的笔意,体现了山势的开合变化;丘壑的主宾、远近、走折均刻画得十分自然并且气势连贯,此图正应了王原祁的一句话“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兼备,。”[注:参见[清]王原祁《雨窗漫笔》。]
同时王原祁对董其昌也很推崇,“一部清代山水画史,不妨视作董其昌思想的注脚,这当然只能从中国绘画本体化进程的‘内在理路’上着眼,并把董氏思想作为一种泛指而成立。”[注:参见卢辅圣《“四王”论纲》,《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王原祁对董其昌的评价是“董、巨风韵,元季四家中大痴得之最深,另开生面。明季三百年来,董宗伯仙骨天成,入其堂奥。衣钵正传,先奉常一人而已。”[注:参见[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董其昌的出现是一个信号。他把程式化的追求推到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杜绝了它自身继续前行的可能性。并且他在审美意识上提出南北宗,在技巧表现上提出南北宗,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使后人很难摆脱他的观念模式”[注:参见陈振濂《清初“四王”的程式与山水画发展主客观交叉诸问题》一文,《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四王是生逢董其昌之后――当董其昌已经把山水画形式反复咀嚼,并已总结出几套极精彩的程式,还从画史(本体理论)方面和书法方面进行强有力的佐证之后,四王们的再沉迷于程式,未免令人产生‘迟暮之感’。”[注:参见陈振濂《清初“四王”的程式与山水画发展主客观交叉诸问题》一文,《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实际上王原祁“龙脉”的提出也恰能证明是董其昌程式的延续,以一种“动态”而全面的谱系观来看这一现象,一方面,师古有其民族文化心理渊源,一方面也许也是源于一种信念即:每一个事物都有其最理想的表达方式。“画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门庭,不可相通。惟树木则不然,虽李成董源范宽郭熙赵大年[注:董其昌认为显然是指赵大年而非赵伯驹。]赵千里马夏李唐,上自荆关,下逮黄子久吴仲圭辈,皆可通用也。或曰:‘须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虽复变之,不离本源,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王原祁“龙脉”的提出,同时也是试图寻找布局中的最理想的表达方式。
篇(4)
关键词: 沈括 山水画 “以大观小” 透视
在沈括的画论中,对后世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以大观小”之说,这也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沈括之后八百多年没有人细谈过“以大观小”,只是近代才开始有专门论述,讨论的焦点就是一个透视的问题。
中国画画论上多把“以大观小”归入到“章法”中讲,现在选出几种论述较为详细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以分析。
蒋立群认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现代意译应为――远焦反点透视法。换句话说,‘以大观小’包含‘远距透视’和‘反点成像’这两个相互依存的内容,组成中国画透视科学体系的主体。”①又进一步解释说:“远距透视(科学原理)、反点成像(创造运用)和创作方法(艺术思维)的统一,这就是‘以大观小之法’的全部外延和内涵。”②他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得也很详细,讲出了“以大观小”是什么,大胆地提出了新的理论猜想。其出发点是在寻求怎样用现在的语言把古代的画论阐释出来,这就不可避免要受外来词汇及其思想的左右。人们批评他大多都是认为他关于中国画“透视”的理论过于简单,不能涵盖“以大观小”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内涵。
洪再新认为:“在绘画审美上,‘以大观小’说被认为是用心灵的眼笼罩全景的主张,它服从艺术上的构图原理,并不服从科学上算学的透视法原理。”③(沈括)“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博学多才之士,对绘画的透视构图未必真的有多少研究,而只是凭着一时兴趣,凭他综合的思维方式,循着‘造理入神’的‘妙理’,直觉地发现与李成得出的经验之间的差异。他耐人寻思地变换了观察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说,以‘观假山’的视觉经验,否定了‘掀屋角’的感觉,进而否证了李成透视经验的普遍性。这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常识并不可靠,经验的局限性也很大。这样,我们对沈括‘以大观小’说是什么就有了认识的范围。我们不是去争论它和‘仰画飞檐’的谁是谁非,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不同于李成的经验陈述,一种发展了李成经验的理论。”④他从理论产生的动因上引出问题,指出沈括有大量的制图学经验,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对近五十年来的研究观点总结出正负两种作用。他很有洞见地发现:“理论的价值随着参照对象的转换而变化,但是产生该理论的原来的参照却未被提及。”⑤“以大观小”比“仰画飞檐”包含更多的文化信息,正是由于它是提出疑问的理论,具有理论所应有的活力,因此能在八九百年后重新为世人所关注,具有独立的价值。洪再新不去追究“以大观小”是什么、不是什么,而是站在理论创建的高度,对“以大观小”近五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倡导回复理论的权威,建立理论的独立价值观,“证伪试错”⑥的历史才能显出创造性,使理论之树常青。
刘继潮认为:“这里的‘山水之法’,不是实指画家在真山水中具体的可实践的观察方法,也不是指山水画具体的描绘方法,而是指成就中国山水画独特图式的思维之法。”“首先应该明确认识到,‘以大观小’不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在现实中可实际运用于视觉的观察方法。”“其次,‘以大观小’纯粹属于古典山水画家创作中,整合视觉意象、创造性想象的心理过程或心理现象。”“显然,‘以大观小’只是一个比喻,一种想象,一种思维智慧。”⑦“‘以大观小’式的神游,与散点透视和动点透视的对景写生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大观小’式的神游,内含着视觉感受――意象积淀――想象整合。”⑧“‘以大观小’是对‘山有三远’的理论回应、发展与升华。沈括在‘以大观小’的论述中,廓清了古典山水画创作中不同层面的问题。沈括清醒、明确地发现‘以大观小’是古典山水画空间结构的统摄之法。想象是‘以大观小’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说,‘以大观小’的‘妙理’,就是对客体自然的超越,对视觉真实的超越,对主体生理局限的超越。也就是对焦点透视的避与取消。自沈括批评李成‘仰画飞檐’之后,古典山水画中几乎没有再出现类似局部焦点透视与整体不协调的现象,从中不难体会沈括批评的潜在理论力量。”⑨“在‘以大观小’的统摄下,古典山水画家创造性地将自然的远近关系转换为画面的层次关系,将物象的结构关系转换为肌理的形式关系,将物理关系最终转换为审美关系。”⑩如果说洪再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唤理论的创新的话,那么刘继潮的这篇文章可谓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创新。刘继潮竭力用中国本土的语言来论述中国的问题,在山水画空间上找到富有智慧的“以大观小”而总揽之,系统地进行论述,中西对比研究,努力架构一套与西方平等的,但又不受外来影响的话语体系,竭力避免使用外来词汇,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成功的。他对“以大观小”所含有的文化含义都一一道明,其阐释是对权威性绘画史、绘画理论发展史、山水画史等忽视沈括,以及中国画出版物在论中国画空间时充斥着“散点透视”、“动点透视”等的有力回应。他和蒋立群都是试图创建一套理论来解释“以大观小”,只是一个采用,一个不采用外来词汇,来阐释中国古代的画论,相比较而言,刘继潮的理论更中国化,其中能够包含众多的文化元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但都不是专门论述“以大观小”的,或是论述得不够具体。俞剑华论述李成“悟远近透视之法,山上之亭馆,仰画飞檐,盖宋时对于远近明暗等法,已有相当发明,惜后人不加研究,妄谓画山水乃以大观小,遂置透视学于不顾,故宋以后之山水画离自然实景,愈趋愈远,而终不免陷于空想杜撰者也”。{11}洪惠镇《山水画三远法别解》一文将“以大观小”和“三远”结合起来讨论,指出“以大观小”之法实际上是三远法的基础。王伯敏认为:“艺术创作上的这种‘以大观小’的推远看,在中国山水画的表现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推远看’,对于绘画创作,至少可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第一,推远看可以解决透视上产生的某种矛盾。第二,推远看可以帮助画面的置陈布势。”“中国山水画中的楼阁,画家总是把它推到中景或远景来描绘。把原来成角透视变化较大的,尽一切努力使之减弱到变化最小的程度。”{12}李少文认为:“沈括所举‘以大观小’法,正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独具的观察方法和艺术手段。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山水画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要求用有限的面积变现最大限度的空间――全景山水。打破固定视点和有限视野的限制,放开画家眼界,代以游动的视点,……以造出可望、可游、可居的艺术境界。这种理论正是为着迎合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摸索出的一整套鸟瞰式透视的特殊规律和表现方法。”{13}
之所以今人有这么多的论述,其产生无不是因为西方透视学的冲击。纵观这些观点,正像洪再新说的那样,“它具有的传统文化的复杂涵容,在今天都有待于新的反思。只要它暴露的问题越多,它的理论价值就越明显”。{14}他还特别提出应注意理论产生时最初的参照。《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马不画细毛》中,沈括是这样论述的: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余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余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盈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奚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按:画横线的字为笔者标出)
依照沈括的论述,“马不画细毛”中的“以大为小”与山水画“以大观小”是有联系的,因为中间有一个“又”字衔接,所以今人在论述时不能隔开而论,这一点应该注意。“以大为小”、“以大观小”同为中国画的画理,同是对艺术规律的认识。
学者们在论述时出发点不一样,谈论的重点有别,多数是在论述李成时提到沈括对“仰画飞檐”的非议,专门系统论述“以大观小”的并不多。有的学者认为“仰画飞檐”就是一种焦点透视,有的认为古代中国画画论应用自己本土的元素和思维方式去阐释。沈括是在具体谈李成“仰画飞檐”时提出山水画的“以大观小”,但他自己并没有更深入地去论述,他的观点没有给出一个系统的“以大观小”的理论。因此需要联系上下文本的关系,才能更明确沈括在说什么,在论述他的观点时才能更全面。
注释:
①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80.
②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34.
③蒋立群.解开中国画透视之谜――兼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科学性及艺术创造性.美苑,1986,(5):28.
④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8.
⑤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7.
⑥洪再新.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新美术,2007,(5):15.
⑦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49-50.
⑧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0.
⑨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1.
⑩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53.
{11}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175.
{12}王伯敏.中国山水画“七观法”诌言.新美术,1980,(2):45.
{13}李少文.空间、时间、空白――学习民族传统的点滴体会.美术研究,1981,(1):57.
{14}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29.
参考文献:
[1]胡道静整理,沈括馔.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
[2]蒋立群.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美术研究,1986,(4).解开中国画透视之谜――兼论沈括的“以大观小之法”的科学性及艺术创造性.美苑,1986,(5).
[3]洪再新.理论的证明,还是理论的发现――沈括“以大观小”说研究评述.新美术,1986,(2).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历史平台――宋代美术诸问题的艺术史意义.新美术,2007,(5).
[4]刘继潮.建构古典山水画空间理论的话语体系――释“以大观小”的思维智慧.美术研究,2004,(2).
[5]洪惠镇.山水画三远法别解.美术研究,1998,(4).
[6]王伯敏.中国山水画“七观法”诌言.新美术,1980,(2).
[7]李少文.空间、时间、空白――学习民族传统的点滴体会.美术研究,1981,(1).
[8]陈红.浅析“以大观小”在中国山水画中的作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9]魏舒梅.感悟中国画之“以大观小”.艺术教育,2006,(11).
[10]曹明.“以大观小”的再“观”.美与时代,2006,(10).
[11]王石礅.从以大观小谈绘画透视学.美与时代,2007,(10).
[12]樊莘森,高若海.从“仰画飞檐”和“以大观小”的论争谈起.文艺研究,1981,(1).
[13]陈绶祥.近大远小 以大观小 变时变空――中国画透视刍议.美术,1982,(7).
[14]华强.对沈括“以大观小”真义的阐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1).
篇(5)
【关键词】:山水画;萌芽;发展;画派;风格
【中图分类号】G622
山水形象作为描绘对象远在西周时期就在帝王的冕服、玉器的装饰纹样中就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山川形象作为人物画的装饰背景出现在画面之中,如汉代的画像砖《煮盐图》画面中山的形象占据了大半空间,但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并不是山,而是制盐的过程。直至魏晋时期,山水的形象才由背景变为主题,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画坛。东晋画家顾恺之所做的《女史箴图》中出现了结合完美、表现真实的山林、鸟兽等元素,画家以俯视的角度用丰富的线条来表现山峦的变化,创造了山水画的表现基本技法,为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崇尚老庄清淡玄学的兴起,江南秀丽的山川激发了画家的创作激情等因素使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勃然兴起,以老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玄学造就了艺术家们简淡、玄远的审美观,并出现了一批擅长山水画的画家和山水画作品及第一批山水画论文,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但我们从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这两篇重要的山水画文献中,可以体会到当时山水画发展的水平。宗炳的"畅神说"及王微的绘画观点不谋而合的强调了主客体的融合,自然与精神的合一,这些理论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画坛,顾恺之、宗炳、王微等画家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先河。
隋唐时期山水画在南北朝萌芽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展子虔的《游春图》被张彦远誉为"唐画之祖",此画在透视关系上不仅表现出了空间的一般关系,也注意到了空间的深度,画面有"远近山川,咫尺千里"之感。同时该画在表现技法上也极具特点:山以单线勾勒,填以青绿,用笔工整,傅色浓烈深沉,为唐代青绿山水画一派开了绪端。盛唐以后经过一批艺术家的推波助澜,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派和以王维、王墨、张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派,李思训及其儿子李昭道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一系画风,他们的画对后世青绿山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追随者,被后人推之为"北宗"或青绿山水画之祖。王维继承了吴道子画派画风并创造了"破墨山水",强调水墨在山水画中的重大作用,把水墨山水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被后人推崇为"南宗"之祖。中国的山水画发展至唐代终于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从此,大河奔流,滔滔不绝。
五代及两宋时期,山水画家辈出,但由于眼光所限,人与自然的那种娱乐亲切的牧歌式宁静成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基本音调,五代的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几位山水画大师在继承传统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各自对山水气势的体悟,北方画派代表荆浩、关同的画构图巍峨,画风雄浑,同时,荆浩所做的《笔法记》为后世山水画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南方画派代表人物董源、巨然所画山水山势高耸,但结构圆浑,布局宏大,无雄奇冷峻之感,画面浓淡交错、点线并置,画面具有内在的韵律之感。五代时期南北两派的这几位画家对后世绘画影响巨大,其山水画艺术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为后世艺术家所继承和发扬。宋初山水画以李成、范宽、关同为主要代表,这三家皆师于荆浩,注重师造化,后人概括说:关同峭拔,李成旷远,范宽雄杰,足以见得他们在山水画上取的巨大成就。北宋统一全国后,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融进了新的江南画风,出现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郭熙初学李成,后师各家及自然,创造了自己雄壮、深远的绘画风格,他所著的《林泉高致集》是我国画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在绘画中表现山水在不同季节、气候下不同的面貌。徽宗时期又有一个新的画派异军突起,即"米点山水",首创人米芾,他画山水多用水墨点染,不拘于形色的勾皴点染。他的儿子米友仁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画法,并有作品传世。北宋中后期,一些山水画画家为了迎合宫廷的欣赏趣味,创造了典丽的青绿山水画,是青绿山水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典型代表画家有"大青绿"王希孟及"小青绿"赵伯驹等人。南宋时期虽国家偏安一隅,但绘画艺术的繁荣仍不亚于北宋,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一角半边"的山水画新风,对后世山水画影响极大。总之,北宋山水画画风雄浑、深沉,崇高胜;南宋山水画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
篇(6)
维特鲁威在书中提到三种类型的布景:一是悲剧,一是喜剧,一是森林之神滑稽短歌剧。它们的装饰不一样,要根据不同原理进行构思。悲剧布景用圆柱、山墙、雕塑和其他庄重的装饰物来表现。喜剧布景像是带有阳台的私家建筑,模仿了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致,是根据私家建筑园林设计的。森林之神短歌剧的背景装饰着树木、洞窟、群山,以及所有乡村景致,一派田园风光。[1]11414世纪,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乔托(Giotto),他摒弃了中世纪绘画的程式化、平面化、装饰化的风格。他在1305年创作的壁画《逃往埃及》中把写实技巧与透视方法应用到绘画上,力图使人物与自然交融会通,构图层次分明。乔托的绘画开启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为后人奠定了基础。
“15世纪,透视学在意大利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论文著作相继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属于透视的发展期,出现了大批的艺术巨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建筑师布鲁涅列斯奇(FilippoBrunelleschi)的‘聚向焦点’透视体系。意大利画家、建筑师阿尔贝蒂(LeoneBattista)利用平面和侧面来表现透视原理,他是第一个给透视规律作正式叙述的人,创造了透视网格法,著作有《绘画论》。对透视学最有贡献的是画家弗朗西斯卡(PierodeiiaFrancesca),在他的作品《康司坦丁之战》《基督洗礼》《理想城市》中可以发现他对几何和透视的研究。弗朗西斯卡晚年致力于数学与透视研究,并撰写了《绘画透视学》,书中系统、完善地阐明了用地面平面图作透视图的方法。”[2]到了文艺复兴极盛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在研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许多有关透视方面的理论文章,后人将其整理成《画论》出版,《画论》将透视比作“绘画的缰和舵”[3],并将透视分为线透视、色透视和隐没透视。与达•芬奇同时期的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Durer)专程到意大利学习透视学,对线透视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形象地阐述了透视方法的基本原理,丢勒在其著作《圆规与直尺测量法》中创立了分格画法,并且把几何原理很好地运用到透视图中,他的透视原理被后人称为“丢勒法”。17世纪法国里昂建筑数学家沙葛(Shage)的《透视学》制定了几何形体透视投影的正确法则。18世纪末,法国工程师蒙许创立的直角投影画法,完成了正确描绘任何物体及其空间位置的作图方法,即线性透视。今天知晓的透视图法及其依据的全部原理,是由英国数学家泰勒(BrookTaylor)在1715年出版的《论线透视》一书中所确立的。该书除了论述一点透视外,还阐明了前人未曾涉及的二点透视和三点透视。透视学从产生到成熟,极大地促进了透视布景的发展,它为布景画家提供了创造三度空间的重要手法。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艺术思想及绘画艺术与透视布景的发展
14世纪至16世纪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遍及欧洲各国。文艺复兴即是人文主义战胜中世纪的神学及对古典文化的复兴。此时的意大利人文戏剧体裁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都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戏剧开始反映人生反映自然,这从客观上导致戏剧布景必须以写实手法去描绘表现人生环境和自然环境,以获得相应的舞台视觉效果,而透视法伴以明暗的立体画法则成了唯一的最适合的手法。从而,透视布景开启了戏剧舞台背景的全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壁画艺术创造汇聚了一大批艺术造诣高超的艺术家,如乔托(Giotto)、马萨乔(Masaccio)、达•芬奇、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拉斐尔(RaphaelSanzio)等一大批巨匠为意大利各地的建筑和教堂绘制壁画,而这些壁画都是在远距离或空旷的空间里,幅面较大。在绘画的技法上大都利用透视原理表现三维空间。壁画的面积较大,使用大量价格昂贵的材料会产生过高的造价,因此一般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矿物质。透视布景的绘画同样也是在面积较大的画面上绘制,而且不是永久性的,因此无须采用价格昂贵的颜料。透视布景和建筑壁画都是在一定的空间里展现,壁画的创作技法和透视布景的创作技法相似,都在色彩、透视、素描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壁画的创作技法为透视布景的发展提供了艺术处理与技术运用上的基础与经验。同时,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学的发展与运用,激发了绘画艺术家对舞台艺术的浓厚兴趣,他们的绘画艺术造诣直接推动了舞台透视布景艺术的发展与提高。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布景决定性的创新是在16世纪初。在罗马和费拉拉的戏剧演出布景的处理中,布景开始强调整体场景。例如,对房子的处理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体表现街道的空间环境。意大利的费拉拉画家乌地尼(GiovanniDaUdine)、画家金加和建筑家、布景画家皮鲁兹(PeruzziBaldssare)成功地将透视学原理用于舞台的绘景上。1518年乌地尼为《卡莎布拉》设计布景,金加于1508年在乌尔比诺设计《卡兰德利亚》布景,皮鲁兹于1514年在罗马设计《卡兰德利亚》布景,他们均用透视法结合明暗关系创造出具有无限空间的幻觉布景。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三位绘画巨匠也都曾经为戏剧舞台画过布景。他们运用透视技法把绘画中的构图、色彩、明暗、质感等绘画造型元素综合运用到舞台布景的创作中,绘制出富有空间感的精致、逼真的舞台布景。这也为后来的戏剧舞台布景———巴洛克布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54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谢里奥编著的《建筑论》可以称为第一部舞台布景教科书。谢里奥在书中根据维特的《建筑十书》中叙述的布景设计图,分别绘制了“喜剧”“悲剧”“田园剧”三种布景设计图。这三幅设计图的景物线条都是向远处的中心灭点集中,这样有助于深度空间的体现,能够在舞台上产生纵深的幻觉。谢里奥根据维特鲁威所描述的罗马剧场稍加改变,舞台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为演员表演区,后面则是用来布置透视布景的区域。景中所用的透视技法为一点透视,景区地板前低后高,地板绘上方格,随着透视的原理变化,格子逐渐缩小,向布景中心灭点汇聚。谢里奥的布景是固定的,其中前景是立体的,后面的景物按照透视逐渐缩小。当需要切换布景的时候,立体的布景就必须让位二维的平面,让透视布景完全统治舞台。这就导致了后来被称为镜框式舞台的舞台样式形成。
镜框式舞台与透视布景的发展
镜框式舞台的出现与形成是透视布景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镜框式舞台的形成时期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说法不一。在镜框式舞台没有产生之前的戏剧舞台布景大多采用同台多景或连台多景的形式,每个景片虽有一定的透视空间概念,但整个舞台不是由一个焦点透视组织而成。戏剧史上第一座室内专用剧场是意大利维晋察的奥林匹克剧场,这座剧场是由专门研究维特鲁威著作和罗马剧场建筑遗址的建筑师帕拉奥迪负责设计而建造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使用透视布景,受当时透视法的影响,剧院舞台改造成了立体的透视街景,台上的每位观众至少可以看到一条深远的街景。自奥林匹克剧场建成,人们开始了对透视布景和写实舞台的追求和发展。1561年,奈罗尼(Naironi)用塞里奥式布景在锡耶纳教堂广场为《洛丹索》设计了舞台,他打破了观众席和舞台连接的传统做法,用一个镜框台口把它分割开,使整个舞台看上去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也许这是最早真正利用镜框舞台的布景资料。1618年修建至今仍然保留的意大利帕尔玛的法尔内斯剧场是现在幸存的第一个永久性镜框式舞台的剧场。镜框式舞台的出现,透视布景就可以按照焦点透视原理设定视平线,准确地表现舞台透视空间,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幻觉,以达到烘托戏剧气氛的效果。可以说“镜框式舞台是顺应透视布景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它的出现也促进了透视布景的发展”[4]。
舞台换景技术革新与透视布景的发展
描绘性的布景出现后,形象的真实性限制了舞台空间,在视觉上原来静止不动的布景已无法适应舞台的演出,必须通过不断地换景才能体现剧情的发展。因而,以前那种浮雕式的布景逐渐被可移动的布景代替,这为侧幕体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欧洲最早的舞台机械装置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当时威尼斯的造船业已经十分发达。每当新船完成以后,造船技师都要进行一些特技表演,他们会用娴熟的技术来博得大家的开心。在威尼斯造船业萧条的时代,这些在造船技术中广泛运用的滑车和绳索被引进到剧场运用于舞台上。这些技术为舞台切换布景提供了技术保障,透视布景因此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迅速地变换。这些舞台技术的使用与改进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透视布景的运用与发展。
侧幕体系布景产生对透视布景发展的影响
1600年,数学家朱杜巴尔多(Guidubaldo)在其出版的《透视学》中,其中一节专门论述了有关舞台美术的内容,论述中第一次真正地分析了透视布景的一些难题并作了一些解决方法,如怎么样在平片上绘制建筑物的两个面,这种全新的舞台布景形式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1606年,阿里奥蒂(Aliotti)根据朱杜尔巴多的原理,以高超的绘画艺术和完善的透视技法,绘制出了全部由平片侧面布景组成的布景,这便是侧幕体系布景。[5]侧幕体系布景特点是:由侧幕、檐幕、背景幕三个部分组成,三个都可以根据剧情需要迅速切换。舞台两侧有绘画的景片,每个侧面景片位置有多幅景片,换景时只需移动景片。舞台的后面,是一块画有透视布景的画幕,这块布景构造通常有明显的透视感,檐幕和侧幕部分的画景与其透视线相衔接,形成透视上的统一感。由于这种布景容易切换、富于变化,能够极大地丰富舞台布景的表现效果,因此很快开始流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透视布景的发展。17世纪至19世纪的剧场中,侧幕装置一直是布景中最重要的,也是被使用得最多的布景样式。
透视布景的兴盛
17世纪,剧场艺术开始追求舞台布景的幻觉性,意大利的透视布景被欧洲各国广泛采用,透视学的发展日趋完善,镜框式舞台,侧幕体系布景的产生,快速的换景技术等在欧洲各地成了共同的形式。18世纪,透视布景依然盛行欧洲戏剧舞台,但此时的透视布景还是一点透视的形式,特点是规模大、布局对称,体现了一定舞台的深度空间,但画面缺乏灵活变化,而且演员不宜靠近布景表演。直到巴洛克布景的出现,这种状态终于开始得到改变。巴洛克布景是18世纪戏剧演出日益盛行时产生的。演出业的兴盛使舞台布景显得越来越重要,其在整个舞台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场面越来越豪华,细节装饰越来越精致,这吸引了大批巴洛克风格画家和建筑师参与其中。此时的舞台布景宏伟壮观、充满动感、起伏波动,精湛的透视变奏,戏剧性的构图,体现出无限的深度空间,使布景画面产生统一协调的、如巴洛克绘画的艺术风格。意大利当时是巴洛克透视布景师的集中地,而且他们世代相传,形成布景世家。其中比比艾纳家族在透视布景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比比艾纳家族祖孙四代从事剧场建筑和布景设计,并且把意大利的舞台布景及技术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引导了18世纪欧洲舞台艺术的发展。这个家族由乔凡尼•玛利亚•加利开始,他的儿子费尔南迪多(Ferdinando)、费朗切斯科(Frencesco),孙子亚历山德罗(Alessamdro)、朱塞佩(Gius-deppe)、安东尼奥(Antonio)、小乔凡尼(Gio-vanni)以及尊孙卡洛(Garlo),祖孙四代都从事于剧场建筑和布景设计,他们把意大利的舞台布景、舞台技术传遍欧洲各地,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剧场的造型艺术。
作为巴洛克布景的代表,比比艾纳家族的透视布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把余角透视引入舞台布景设计。这是一个伟大的革新,也是比比艾纳家族透视布景对布景艺术最大的贡献。余角透视的特点是有两个灭点,分别在左右两点,舞台上的余点为舞台两侧。余角透视布景不同于中心透视布景的呆板,它在构图上显得灵活多变。演出时,演员可以靠近后景活动,有更大的空间调度,每位观众都可以欣赏到逼真的舞台透视布景。2.改变布景设计一贯的比例。比比艾纳家族在设计表现中压低地平线、增加布景尺度,把建筑处理成以建筑物下部为主,其余部分升入上部空间,以体现建筑物的高度。这样就可以使场景显得特别的宏伟高大。3.划分舞台区域。由于余角透视布景的两个灭点是处在舞台侧幕里,较浅的舞台空间也可以使用,比比艾纳家族将舞台分为前后两个区域,前面区域可以为演员活动用,后面区域则用于表现无限深远的幻觉般的布景。前后舞台的景片利用轮杆系统进行切换。4.比比艾纳家族透视布景体现了巴洛克绘画的风格,画面大多为建筑局部、圆柱、圆拱等曲线物。细节装饰精致,甚至在布景上出现人物。整个画面立体、浩大、豪华、逼真。这种探索启示了无数的继承者,影响了此后100多年的戏剧舞台。“比比纳家族的透视布景所具有的那种精湛的技巧和无比的耐心,那是现代舞台美术家所望尘莫及的。”[6]18218世纪除了比比艾纳家族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透视布景家族,如马罗(Mauro)家族,主要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主要戏剧中心工作;奎里奥(Quaglio)家族,主要在奥地利和德国从事舞台布景设计;加利阿里家族(BernadinoGalliari)支配了北意大利及德国的舞台设计。这些家族和比比艾纳家族一样,利用透视的原理进行舞台透视布景的设计,他们对舞台布景设计的影响深远,整整延续了150多年。
透视布景的衰落
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新兴的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向封建意识形态挑战,产业革命也随之完成。随着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戏剧的观念也跟着发生改变,戏剧的舞台空间观念也期待着新的突破。伴随新的舞台美术观念的兴起,透视布景也随之丧失了垄断地位并最终走向衰落。18世纪末,以历史上第一位现代剧导演梅宁根公爵为代表的戏剧家们倡导布景要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倡导自然主义,最终将生活中的物品直接搬上舞台,导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开始使二维透视布景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灯的诞生开辟了舞台灯光的新纪元,从而舞台美术也进入了新的时代。此后,灯光艺术日益发展,光成了舞台上最重要的造型手段,画景统治舞台的时代基本结束。20世纪初,有“现代灯光之父”之称的瑞士人阿道尔夫•阿皮亚(AdolpheAppia)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靠绘景来表达静止画面。他断论:“光在舞台是最重要的造型手段。”[7]他提倡通过音乐和灯光来组织有变化的节奏空间。阿皮亚认为画景与灯光是相互排斥的、相互矛盾的。阿皮亚还认为:剧本是第一位,它决定演员表演,其次是表演者的动作决定舞台空间布置,灯光处于第三位,处于末位的是绘景。“透视布景的致命弱点在于二维的幻觉画景与三维的实在的演员之间的矛盾。它只有在演员的身体、动作所无法接近和触及的范围内才能产生幻觉效果。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演员的动作范围,并且无法对表演提供实体性的支持。”[6]182比阿皮亚稍晚的戈登•科雷(EdwardGordonGraig)认为呈现在舞台上的布景一定要等协助演员的表演动作的展开。他主张虚拟布景的发展,这一倡导吸引了很多追随者,从而引发了舞台布景运用的新变革。
篇(7)
澍雨是当代青年花鸟画家中的佼佼者。作为北方人,他大学时远下杭州,在南方的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接受本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花鸟画传统基础。而后他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并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相对于一南一北两大美院的教育体系,澍雨都可谓深入其中而又出乎其外;而相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画教育的学院化倾向,则澍雨又具有足够的研究资源与个人能力展开充分的反思。
众所周知,国画教育在中国美术学院渊源有自,自从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以来,聘任了诸乐三、陆俨少、陆抑非、吴茀之等一大批传统派的画家,其训练更偏重于传统和基本功,对中国画教学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思考。人们常常把中国美术学院的国画教育称作“过五关斩六将”,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中国美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的训练体系,环环相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等留学西方的画家则从建院伊始就提出了“用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在蒋兆和、叶浅予、江丰、吴作人等关键人物的实践和主张下,也逐渐形成了中西融合、注重个性的教学思路,对于教学方法的思考远不及对个人创作的投入。这在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习期间就常与同人感慨,目前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理想的学习进路,就是能够在中国美术学院接受本科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后再来中央美术学院读研深造,开辟创作的胆量和思路。所幸这一梦想在澍雨这里成为了现实。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本科学习,让澍雨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源流脉络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掌握,他没有放弃中国美院得天独厚的面对原作的临摹条件,广泛临摹了中国宋元以降花鸟画发展几个关键时期的代表性画家作品,按照导师们的指点将由林良、吕纪、陈淳、徐渭、、石涛直迄扬州八怪、赵之谦、吴昌硕的古代花鸟画传统各个击破,掌握了中国花鸟画工笔、没骨、写意各个画种的全部技法,无论双钩、设色还是水墨都达到了花鸟画科班教育所要求的全面而系统的高度。
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中,他一方面研习古代画理画论,撰写出具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同时也在导师张立辰先生的指导下,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画以笔墨造型语言结构自然生态的学术理念,在理论的指导下逐渐形成自己既源于传统,又与时人迥异的艺术特色。他似乎并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没骨专家”这样狭窄的定位上,而是广泛尝试各种技法,在大幅作品、扇面小品等多种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精品不断问世,毕业创作受到导师组的一致好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澍雨并没有像很多当代花鸟画家那样落入技法的俗套,陷入到那种单纯仰仗程式和概念,缺乏文人气和底蕴,“一说便俗”的境地。相反,他在技法的高度上保守出了笔墨语言的天然之趣。这是一种“拙”而非“野”的意境。用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的话说:野可顷刻立就,拙则需历尽一切境界然后解悟。野者矫揉造作,而拙者则为笔墨尽境。澍雨的笔墨技法,并非是单纯依靠程式的概念化符号,而是紧密围绕物象造型而存在,无论是花卉、兰竹还是翎毛、草虫,澍雨都能表现自如,一钩一点似乎都是为他所表现、精神为之契合的物象而生。读他的作品,能够让人在欣赏其笔墨结构甚至其书法题款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种欲与画面物象对话的状态之中。真可谓笔墨氤氲处,朴实无华,元气淋漓时,浑然天成。
由此我们可以来回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中国画学院教育所带来的艺术生态的变化这重问题。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如果说徐悲鸿、蒋兆和的体系代表了西方绘画理念入侵对于中国画生态的根本性影响的话,那么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事实上潘天寿所开创的“中国画分科教育”的背后,也隐含着中国画生态的一次根本裂变。至此,中国画从传统诗书画印兼修的文人修养,蜕变成连山水、花鸟也要加以区分的现代学科和学院专业。从技法训练的角度,在当今学院教育中这当然是必须的;而对于当代中国画家的命运与选择来说,则这种专业化的后果并不总是积极和光明的。这从今天许多中国画家训练单一、知识狭窄、不通诗文甚至不敢题款等很多现象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样说绝对不是苛责前辈,而是看到,面对20世纪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命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辈学者和艺术家的见解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只能墨守的经验,不如说,是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一个永恒的、开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