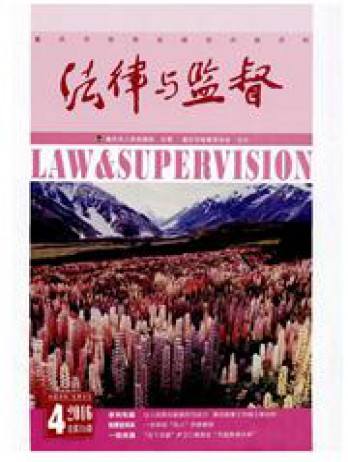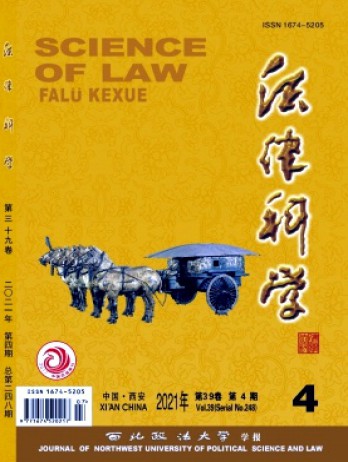法律行为的分类标准精品(七篇)
时间:2023-06-28 16:50:49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律行为的分类标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事实行为,人为事件,区别
在民法中,要产生民事法律关系除需具备主体、客体和相关的法律规范外,还需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促使法律规范从客观权利转化为主观权利,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因,这就是民事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将其和法律后果(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联系起来的具体生活情况。法律事实是反映现实生活情况的存在,具有使法律规范发生作用的杠杆的意义,是把法律规范和具体主体的权利义务联系起来的环节。因此,法律事实伴随法律关系的整个生命过程-产生、变更、消灭。[1]
根据民事法律事实是否具有直接的人的意志性,可以分为事件与行为。其中,事件是指与人的意志无关而且不直接含有人的意志性的事实,反之,就是行为。[2]事件的法律后果由法律直接规定,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内容则既可能是根据行为人意志的内容来确定的,也可能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这与行为自身的种类有关。
一般认为,事件可以分为自然事件(绝对事件)和人为事件(相对事件)。[3]自然事件是其发生与人类的活动完全无关的事实,人为事件则是人的活动引起的,但是在民事法律效果中法律不考虑行为人的意思内容(如,就罢工在民法上的意义而言,罢工工人的主观状态就不是民法关注的内容),即视为该事件中不存在人的意思。
自然事件包括人的出生和死亡、自然灾害、一定时间的经过、天然孳息的产生等;人为事件则包括战争、罢工、动乱等。[4]
至于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的分类,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由于分类标准很多,[5]本文仅从如何区分民事事实行为的角度讨论一下行为的分类问题。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历史和本质
大家公认,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法律事实的一种。但是,在中国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论,至今没有停息。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求助于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历史才能弄清楚。
法律行为的概念据说来源于德国注释法学派,许多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法律行为”概念的是德国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Danielnettelblandt,1719—1791)。[6]而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以近代德国法学大师、历史法学派萨维尼的著作《当代罗马法体系》于1848年的出版作为标志的。[7]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接受了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成果,最早采纳了法律行为的概念。[8] 法律行为之最先成为民法上的专项制度, 则始于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9]由此可见,法律行为制度的出现不会早于19世纪。
从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这些概念的使用,首先是为了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是代表民法向公法主张权利。后来,经过萨维尼和潘德克顿法学的改造,法律行为成为民法科学的基础。[10]现代民事法律行为诞生了。
在法律行为概念业已出现的19世纪,所谓的法律行为,客观上是指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是不包含违法性质亦即为立法所绝对禁止性质的,故而专指主体将自己期望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内心意愿表达出来的适法性行为[11](何为适法性行为,学者也争论不休)。
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意思表示并不全然等同于法律行为,遂又将意思表示仅仅作为法律行为的核心构成要素。 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法律行为概念的最新表述中,无论是“旨在于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之说,或者是“意思之表达不为现行立法所禁止”之义,都是为了限定意思表示才得以出现的附加条件:二是作为法律行为所能够引发的法律后果,事实上“皆以意思表示之内容定之……因此意思表示之问题,遂为法律行为之中心问题焉”。[12]
据舒国滢先生的考察,德文的Rechtsgechaft准确的汉译只能是“表意行为”或如有些学者主张的表示行为、设权行为,与事实行为处在同一位阶;而与中文“法律行为”(在民法中称为民事法律行为)相当的德文是Rechtsakt,它是Rechtsgechaft的上位概念,包括表意行为和事实行为两种。[13]孙宪忠也认为,法律行为一词在德文中本身是Rechtsgeschaft,由Recht和Geschaft构成。Recht本身是法律和权利的意思,Geschaft 本身指的是交易的意思,指权利的转让、让渡等。这个词翻译为“法律行为”不算太确切。因为人的行为有专门的词Handle,跟英文的hand词根是一致的,人的纯粹行为用hand.以个人所为的、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德文中表示为Rechthandlung,从其本意来看,这个概念并没有要求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但是“法律行为”作为一项交易,就必须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因为转让权利必须符合出让人的意思,也必须符合受让人的意思[14](由此,可见翻译与引进外国法律理论的艰难)。
因此,法律行为中应当含有行为人的意志,只有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才是法律行为,其概念可以表述为:民事主体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私法上效果的行为。法律行为的本质是表意行为。
二、民事事实行为
关于民事事实行为的含义,据有关学者的归纳主要有四种:[15]
①只要是行为都是事实行为,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事实行为;
②广义上的事实行为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化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③广义上的事实行为中的合法行为则是狭义的事实行为;
④狭义事实行为又可以分为最狭义的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这最狭义的事实行为被直接以事实行为称呼。
其实,要明确事实行为的内涵就必须有所取舍,如果不作出必要的限制,所谓的事实行为也许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能确定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前述①②③种看法过于宽泛,有的甚至把民事法律行为也包括进去了,而我们恰恰需要一个词来概括除法律行为以外的人的各种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既然,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表意行为,那么依照法律后果是否与表意人的意思内容有关,就可以把民法上的行为分为表意行为和非表意行为。[16]前者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前文引述的舒国滢先生的观点也是一个佐证),后者由于其法律效果不必考虑当事人的意思,属于法律对于一种事实情况直接赋予一个法律后果,可以称为事实上的行为或事实行为。
因此,我认为,事实行为应当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而存在的,在界定了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后,其他的凡不以意思表示决定其法律后果的行为都可以看作事实行为。
三、民事事实行为的区分
1、民事事实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基本分类
我国《民法通则》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一定义着重强调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但未明确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被学者认为有重大缺陷而受到批评。[17]同时,《民法通则》创立了“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避免使用“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因为,大家认为这种说法存在逻辑错误。[18]民事行为则是指民事主体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即民事表意行为。[19]这实际上是用“民事行为”取代了传统上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而缩小了“民事法律行为”在中国的外延。正是这一改变,造成了多年来学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争议。所以,未来的立法应当正本清源,确立科学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结束无谓的争执。
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是从“标准”或“典型”意义上下的,它只能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得到完全的适用,不可能适用于全部的情况。其实,任何定义都是这样,只有找到一个基准点(或稳定态)才可以下定义,而这个基准点常常就是出现几率最高的情况,符合这个情况的就是正常的(常态),否则就属于异常情况(异态)。而所谓“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等违反逻辑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呆板地适用民事法律行为定义的结果。一种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法律对它作出的评价,这种评价与定义的基准点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和基准情况一致的才会被法律认可,否则,它的效力就不完全,不论是可撤销、可变更、效力待定还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些都不违背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也不存在什么逻辑矛盾。同时,这几种情况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它们最终会变成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完全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所以,根本不会有逻辑矛盾,也不存在用语不当的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这样,我们在给现实中的行为“贴标签”的时候,就应当慎重。只有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特征的才是民事法律行为,否则就不是,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如果,可撤销可变更的行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被撤销或变更,那它就是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效力待定的行为,没在法定期间内得到追认,那它就是无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就其实质来说和事实行为是一样的,因此它就属于事实行为。综上可知,法律行为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发展为有完全效力的法律行为,也可以转变为事实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见,表意行为与非表意行为的分类也是应当作出限制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划分的“标准时刻”不是行为做出时,而是其效力确定时(只有这时才是稳定状态)。如果可以产生完全的法律效力,这种表意行为就是法律行为,否则就是事实行为,不管其中是否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样对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作出区分,其分类就是很清楚的,不会再有模棱两可或无法归类的情况出现。
另外,学术上认为,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还应当包括准民事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也不是意思表示的内容确定的法律后果,而是意思表示作出后依照法律规定发生的与意思表示有关的其他民事法律后果。准法律行为可以说是处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之间的一种情况,但就其最终的法律效果而言,一般可以归入法律行为。[20]
至于行为合法(或适法)与违法(或非法)的区分由于采用的是另一个分类标准,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区分没有必然的关系。法律既规范合法(或适法)行为也限制违法(或非法)行为,即使是法律行为,它也可能存在违法(或非法)的目的,法律同样不会袖手旁观,违法(或非法)行为在法律上也会产生后果。因此,合法(或适法)与否也无法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分开。[21]
2、民事事实行为与人为事件
在法律效果上,事实行为和人为事件都是法律直接赋予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一种行为,后者为此种行为的结果。因此,无意志能力人实施的“行为”、造成人为事故的行为等,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算作事实行为,而其结果对于局外人来讲一般就是人为事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区分,反映了事实行为与人为事件的联系,这也说明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只有有限的意义。另外,人为事件一般具有规模大的特点,如罢工、战争,同时,人为事件也不限于事实行为的结果(如,人的失踪就不能看作是失踪人的事实行为)。所以,区分事实行为和人为事件也要具体分析,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
由于事实行为范围广泛,且各具特点,属于事实行为的制度只能分散在法律各处,不象法律行为那样系统。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不考虑行为人的意思而言,违法行为、遗失物拾得、埋藏物发现、发明、发现等在一定程度上皆为事实行为。
在此要特别提到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严格来说是一种事实状态,其产生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事件。如有学者归纳,不当得利的产生可以基于人的行为,也可以是事件的后果,甚至纯粹是法律规定的后果。[22]所以,笼统地说不当得利是一种事实行为是不严谨的。
注释:
[1]「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第537-539页。
[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页。
从后文可以看出,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即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起到区分事件和行为的作用。
[3]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另见,「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第550页。
[4]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鉴于本文的观点与该书有一点不同,所以,剔除了其中不合本文观点的例证。
[5] 关于行为的分类,可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6-178页。
[6]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40517-001715.htm
[7]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8] 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40517-001715.htm
[9]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0]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40811-105148.htm
[11]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页。
因此,有人直接以法律行为称呼古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参见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2]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78页。
[13]李小华、王曙光《民事法律行为不仅为表意行为》,《法学》2001年12期,第46页。
[14] 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40811-105148.htm。
[15]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88-189页。
[16]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7-178页。
[17]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81页。
[18]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19]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83-184页。
[20]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59页。
[21]申卫星《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6期,第43页。
篇(2)
法理学中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是很薄弱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们法理学界对法律行为效力问题的漠视?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与我国法理学界的封闭性、研究的滞后性。
本文希望能在现有的法理学视野范围内为法律行为的效力研究找到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而法律的效力正是这一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对国内现在流行的法理学教材和专著 [2]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这些教材或专著在研究法律行为方面要么只字不提,要么研究的非常少。法律行为制度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法律领域,为什么国内这些专家学者对于此问题会有这样的态度,是由于国内学者的学识水平不够么?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撰写法理学教材或专著都是国内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士。那么是由于法律行为制度本身的原因么?因为法律行为制度本身的属性与法理学的本性相排斥么?如果是的话,那么法理学与法律行为制度为什么会相互排斥呢?对于以上一连串的疑问,我们试图想通过某一个切入点来发掘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理。那么,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耶林说过,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 [3],因此,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秩序的核心问题 [4].那么,我们来试着从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入手来揭示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理学的关系,进而指出法律行为效力研究当中存在的困难,从而找出困难的解决办法。并希望能对法理学上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二、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的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研究法律行为大体上有两种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1、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是由其在民法当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法理学作为法律科学的一般理论,它的研究对象必须对部门法学的制度建立,理念贯彻提供理论指导。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其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程度的密切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法律行为作为民法的核心制度也是最有特色的制度,法理学应当对它的存在有所反应,并且也必须对它进行研究。
2、对于立法者而言,充分理解法律行为的效力,有利于法典的完善。笔者在后文会谈到,我国目前的立法多关注的是法律的应然效力,而对于法律的实然效力、道德效力研究不够。于是,就造成了我国立法过程当中许多法律理念的流失。比如,我国行政立法当中公共参与理念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者制定法律之时没有对法律的实然效力作深入研究,即使个别立法者依靠自己良好的法律素质,也考虑到了法律的实然效力,可是却没有法律实然效力的反馈途径,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法的效力的反馈问题。而没有从制度上构建好这一反馈途径,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的不深入。
3、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的一种,其对法律关系理论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对法律行为进行深入,细致乃至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促进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而从结构上丰富法律关系理论体系,从内容上充实法律关系理论。
(二)现实意义
1、对于当前制定当中的民法典而言,充分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对于完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贯彻民法的私法理念,理顺民法典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对法律行为效力进行深入研究,势必对民事法律行为带来丰富的指导思想。从更深层次促进民法典的完善和发展。
2、有利于贯彻法律的诸多价值和理念。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包含这丰富的法律思想和理念。对于当前的立法而言,充分的法律行为效力理论的研究,无疑对于提高立法者的素质,提高立法的质量,增强司法者的法律意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立法者,司法人员如果对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有充分的知识,那么无疑对于法律理念的贯彻和推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为建设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的人文、法律环境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我国目前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的尴尬境地
正如笔者在文章一开头所讲的,目前国内法理学的研究,对于法律行为的效力来说是相当的薄弱的。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在中国的法理学家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能做到,可以从部门法理论当中将法律行为效力理论提炼出来,就是说,还没有人能概括出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理论。那么,这种尴尬的境地对于法理学者又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状况怎么就使得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呢?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法律行为的法理学定义要求其具有法理学的气质
有法理学者将法律行为定义为:“指能发生法律上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5]”。有的法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行为的广义概念和统语 [6]”。有的法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法律所调整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7]”。也有学者认为:“法律行为乃基于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上效力之行为也 [8]”。也有学者认为:“具有合法权能的人所做的、能够产生特定法律后果的或产生法律上可能且允许的后果的意思表示或意愿宣告 [9]”。从以上这么多的定义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正如李龙教授指出的一样“我国的法学家尤其是法理学家是在广义上使用法律行为的概念,基本上都把法律行为解释为能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或由法律所调整、能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 [10]”。
很显然,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的定义,表明法理学家迫切的想把法律行为提高到一般理论的高度。这样,才能让法律行为制度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当中。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的法律行为的通说定义(法律行为是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法律行为的通说定义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这种定义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实际和理论问题,也没有提供出法理学可资利用的手段来指导具体部门法,而且该定义看起来除了同义反复之外,还有着耍赖皮的嫌疑。这种赖皮就是:明知道我不能把法律行为制度提高到一般理论的高度,仍耍赖把法律行为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当中,而且煞有介事的说法律行为制度是法理学当中重要的领域。那么法理学家为什么,这么想把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当中来呢?我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民法帝国主义 [11]的影响。由于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使得莫多的法理学家把罗马法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备,最伟大的法律。的确,民法以及与民法有关的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经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人的不断加工完善,以致每一个法律人从内心来讲,都自然不自然的生发出对它那种天然般的纯真崇拜,因此对民法及其理论深信不疑。对民法的具体制度也由于对民法的情感而有特别的依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被誉为民法上的一颗明珠,被萨维尼以来的众多法学者推重备至。它所代表和维护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性的最大范围的张扬,至今在法学者心中还不住的激起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那么,就难免我们现在的,不仅法理学者,还有民法学者,甚至行政法学者会对法律行为制度产生如此深厚的情感,以致缺少了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就会认为法律本身就不完满了。
(二)法律行为的内涵却要求法律行为的民法品质
就像前边所提到的,有的法理学者是从意思表示给法律行为下的定义,其引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概念和技术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除了上文提到的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外,这些法理学者为什么非要引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概念和技术来描述、定义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制度呢?因为法律行为制度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最有特色的部分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对于法律行为制度来讲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法律行为制度的生命力、魅力所在,而意思表示的研究,必须借助于民法上意思表示的理论。因为,首先从民法和法理学产生的先后时间上来说,我们认为,先有民法而后才有独立意义上的法理学,因为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规范,法理学的研究以部门法的研究为基础,所以,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天然的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运气和历史必然性。在研究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之后,再进一步抽象出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意思表示,从而完成意思表示(也就是法律行为制度)的法理学构造。那么,意思表示就肯定会残留许多民法的理念,从而在外部容易生发出民法的品质。
综合以上两部分,我们认为,目前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的尴尬境地是与法律行为制度研究的尴尬境地是分不开的。这种尴尬是由于:一边法理学家提不出具有基础性的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不能把它提升为法理学研究的范畴,但是却一再声称法律行为是法理学研究的当然领域;另一方面,法理学家若真要研究法律行为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就不可避免的绕不过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欲剔除民事法律行为的影响,建立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制度,在方法论及内容上又不得不以民事法律行为为蓝版。这种互相矛盾的状况,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的尴尬境地。
四、探求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进路
固然,我国法律行为效力研究进入了很尴尬的境地,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停止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只不过我们应该转换思维,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从而尽可能的揭示出法律行为效力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应该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我们的研究和思考。
(一)着重探讨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
关于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问题,本文不想展开对法律行为效力来源的具体的多层次的研究,而是想说明法律行为效力来源的理论。目的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研究的方向,至于方向下有关的具体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是开放性的,没有最终结论的。笔者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要从哪些方面入手,要研究的都是哪些领域。效力来源只是个研究方向。
目前我国法律学者还没有对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问题作出来实质性的研究成果。而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已经有学者在探讨了 [12].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中来,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问题才能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
(二)着重分析法律行为效力的种类
我们通常理解的法律行为效力的种类是指无效、效力待定、有效、可撤消可变更等等。这种分类只是从效力的外在形态来分析,而且这种分类明显的带有民法学的气质。当然,在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讨论可以作出如上分类,只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分类,而且那样的分类更有助于我们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法律行为的效力种类就只有无效、效力待定、有效和可撤消可变更么?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标准来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新的分类?笔者对西方法理理论考察后发现,对于法律效力而言,他们通常都将法律效力分为“应然效力”“实然效力”“道德效力” [13].那么我们不管这种分类能否穷尽所有的法律效力类型,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讲,真正有帮助的是他们研究的视角,是他们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他们具体研究的结果是否与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同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也可以研究他们的应然效力、实然效力、道德效力。而且这种研究有部分学者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应当从效力来源和效力种类来进行。而且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对法律行为效力更深层次价值的揭示,才能发展、完善法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制度。
五、法律行为的效力=法律的效力?(一种可能的出路)
对于我们法律人而言,根据一般的法理素养会认为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可能等同。因为,法律行为是法律的一个下位概念,也就是说法律包括了法律行为制度的所有内容。说法律行为的效力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有以偏盖全之嫌,而且持这样观点的人往往还不在少数。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人类的文明、历史发展一再地证明的确如此。笔者认为法律行为的效力其实就是法律的效力。理由如下:
(一)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的客观要求
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 [15].那么很显然,人们的行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根据法的定义,并结合概念和语言使用的习惯来看,在不同层次上,法可以被理解为具体的法律规范,也可以被理解为法律规范组成的体系 [16].也就是说,法和法律规范是相同的事物,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特征 [17].由此,我们说法律规范的效力也可以称为“法律的效力” [18].
法律的效力其实质就是指法律对人们行为的拘束力,不论这种拘束力来自哪里。而在实际的法学研究中,我们往往研究这种拘束力的来源问题,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种关于法律效力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很多情况下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凯尔森认为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基础规范”,然而这种基础规范的效力又来自哪里?凯尔森认为基础规范是不证自明的具有效力,它的效力来自它本身。显然,他的这种学说有欠说服力。它最终导致了把效力来源归于上帝或更高的抽象意义上的某种不能认知的事物,从而陷入了不可知理论的窠臼。哈特认为法律效力来源于承认规则。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的效力来源于自然、理性、上帝等等。我们在这里无意于探讨法律的效力来源问题,正如德国著名学者霍恩指出的,“有关法律效力的理论主要是关于人们遵守法律的理由” [19].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法律的效力仅仅是对人们行为的拘束力,是人们的行为在法律视野范围内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行为在法律上有意义的描述。回过头来,法理学界对法律行为的通说是:法律上有意义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法律的效力问题与法律行为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法律的效力是从立法者的角度确认或认知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的效力则是从守法者的角度来表述法律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行为的效力具体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可以统一于人们的行为,统一于效力问题。
(二)是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现状的客观需要
前文已经提到了,我国法理学界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研究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境地的出现,是由民法情感和民法帝国主义的交叉作用产生的。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法理学界还没有找到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理论,还没有找到沟通法理学与具体法律行为制度的桥梁。那么这种桥梁在哪里?通过对法理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基点的分析,我们认为,法律的效力领域就是连通法理学与法律行为效力的桥梁。当然,效力领域并非唯一的桥梁,只不过是,我们认为在当下研究法律行为效力问题的一个出路而已。
六、结语
我们认为,要想在法理学视野范围内研究法律行为制度的相关问题,就必须总结出能够指导具体法律部门法律的具有一般意义的法律行为制度。如果,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制度根本不能指导部门法,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就是法律行为制度不应当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当中。但是,法律行为制度研究领域及其成果的缺失,并不能阻碍我们对于法律行为效力问题的研究,因为法理学虽然在法律行为整体制度研究方面存在着真空状态,但是法律效力的研究却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即使国内学者没有提出什么完整的法律效力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外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可以拿来用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就更应该以开放的姿态来研究法理学。
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快建立我国本土的完整意义上的法理学,也就是说建立我国的法理学科学,这种法理学应当包括了一切法律领域的所有一般理论问题,不能存在一般理论研究的死角。然而目前受到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下,人们的普遍热情都投入到了“制定一部二十一世纪最科学的民法典”当中去,就更应该提防民法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部门法的研究超越法理学研究的状况,否则,我们的法理学就会有被部门法研究侵蚀、包容的危险。所以,当下,特别要排除民法帝国主义在法理学领域当中造成的不适当影响。
(二)仅仅就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在法理学范围内研究此问题,可以通过把法律行为的效力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来实现。也就是说要用法律的效力领域内的丰富的法律思想,来指导具体部门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虽然用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最起码,它是一种当下法理学研究此问题的一种思路。一种思路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我们能否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问题。
「注释
[2]这些教材或专著包括: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二版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周永坤著:《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1987年版 华夏出版社 105页
[4] 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1996年版 法律出版社 365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6]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7] 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8] 袁坤祥编著:《法学绪论》,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
[9] 《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93页
[10] 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1页
[11] 此处的民法帝国主义仅仅就民法的理论和具体制度设计、技术对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而论。与徐国栋教授的观点不完全相同。
[12] 李永军教授《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80——239页。李军博士《法律行为的效力依据》载《现代法学》2005年27卷第1期。
[13] 参见魏德士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8——150页
[14] 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1996年版 法律出版社 第365――376页
[1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第58页
[16] 刘作翔主编《法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69页
[17] 同上书
第69页
篇(3)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一些民事诉讼中却因为在现有框架中无法找到准确的法律地位,最终因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由于这些纠纷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要求所有业主都参与诉讼的难度大甚至不可能;而且当业主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有部分业主强烈主张诉讼,有部分业主因种种原因不愿意进行诉讼,从而造成住宅小区业主“打官司难”。业主委员会是否可以以自己名义代替全体业主提起诉讼,是长期以来法律界争议的。
本文对该问题作了如下思考:
从民事主体的看,民事主体一直是一个私法中的概念,并且内涵随历史发展而丰富。而我国现有民事主体的分类和我国民法的本质是不可分离的。由于民法通则其本质上较多的体现了主义民法是“公法”而不是“私法”,而最终了“民事主体”的类型;同时又因为在法律行为和合同领域,把合法性定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性,最终导致“法不赞同即非法”的逻辑关系,与私法“法不禁止即合法”本质相去甚远。在这种逻辑推理下来,业主委员会是不太可能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
“特定功能是民事主体确立的重要依据”。某种社会组织是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应是立法者在权衡“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两方案的利益得失之后,实施特定立法政策的结果。因此,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不是社会组织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决定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赋予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地位。
民事主体制度在特定功能的内在推动下,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民法史说明了这一点,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关键词:私法、民法、民事主体、业主委员会
由业委会是否属民事主体引起的思考
一、民事主体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我国现行民法的继承渊源
业主委员会被判定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如果就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讨论,想必必然有很多理由,脱离开民事主体的历史根源于我国现行民法的继承渊源,,也许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根本没有必要去找答案了。
(一)民事主体是私法中的概念,其种类随历史发展而扩张
在古罗马,对于人来说,自由民中能够直接行使主体权利的只是家父。因为在当时,只有家族才是基本的社会单元,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家族作为交易对象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个人实际上被家族所吸收。因此法律只承认以家父为代表的家族为民事主体。但随着商品的发展,势单力簿的单个自然人在某些方面已难以胜任,必然出现自然人的联合。这种联合的最初方式是合伙。合伙具有集中资金、集中智慧以及合伙成员相互信任等优点,使之稳定地存在数千年,仍然是市场中的重要一员。但合伙的最大缺憾是:投资人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确实加大了投资人的风险。另外其对人际关系的过分依赖,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为了克服这些弱点,划出独立于投资人的单独财产归"合伙"这一团体所有,并以此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这样,法人出现了。随着法人规模的不断扩大,法人突破其自身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设立一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可见,历史发展表明,市场主体由自然人单一主体发展到自然人、合伙、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等多元主体。
与之相适应,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制度也从承认单一主体到承认多元主体。1804年法国民法典,仅有关于自然人的规定;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首次承认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但德国民法典不承认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团体的法律地位,将他们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顾名思义,这些社团没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是,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承认其他组织具有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德国法院也通过法律解释,回避了民法典中不承认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规定,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需求。从原始共同体到个人的历史演变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是对人性的解放和对人性的尊重。原始家庭共同体的存在是以牺牲个人的独立主体资格和独立利益为代价的,它禁锢了个人的自由,更无所谓个人的平等问题,在根本上有违人性的要求。于是,自罗马法开始的个人主体资格的确认制度逐渐使个人摆脱家庭、氏族等共同体的禁锢与控制,取得了独立的主体资格,获得了地位平等和行为自由,这些变迁在对个人解放的同时,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的价值取向。
所以,讨论民事主体的问题,抛开“民事主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有可能否定“民事主体”概念形成的本质,从而有可能否定对人性尊重这一价值取向。
(二)我国民法的“公法”性使业委会失去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基础
“民法是私法而非公法,民法应当体现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等私法理念。”
新成立以后,我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事立法上废弃了旧的法统,转而继受前苏联的民法,因此前苏联的民法及其民法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当属民法非私法的观念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渗透。
社会主义民法非私法的观念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上,除了主体平等原则外,意思自治原则和私有财产神圣性原则都受到批判,代之以服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民法非私法的观念体现在具体的民事制度中。在主体制度上,以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的“公民”概念取代私法上“自然人”概念,反映了民事生活的“非私法性”;废弃私法人和公法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传统法人分类,采取法人和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分类,把作为公法人的国家机关法人以及具有公法人性质的事业单位法人混同于民法上的私法人,导致法人分类上的公私不分;对于企业法人,采取所有制分类法,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造成企业的不同身份差别。在物权制度上,把他物权单纯看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只规定所有权而不规定物权,立法上不再使用“物权”这一概念;在所有权的分类上,以主体(即所有制)为标准,将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地位,单一地强调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由于缺乏公、私法人的严格划分,致使民法无法实现描绘市民社会界域、制约公权力对私权利不当侵夺的功能。不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不仅会造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混淆,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而且还会造成不同法律部门功能和作用的混淆,既不利于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有效制约公权力的行使,也不利于保障民法在规范民事主体和保护私权的作用。
业主委员会的实质就是某种私权力的拥有者或者人,由于私权力的不被承认,也就失去了确认其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基础。
(三)我国民法以“合法性”代替“意思自治”关闭了承认新类型民事主体的大门
在我国民事立法以及民法理论上,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意思表示”。《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至于“意思表示”,学者们认为只是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要素”。对于“意思表示”和“合法性”二者在民事法律行为中谁更为根本的问题,我国民法理论明显地倾向于后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民事行为尽管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但该行为能否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即是否具有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民事法律后果。
由于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违法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是“意思表示”还是“合法性”,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标准和不同的自由观念。
篇(4)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不作为行政行为;法律行为
一、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及法律性质研究现状“行政不作为的概念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对于行政不作为的概念有很多学说如法律义务说,法定职责说,违法性质说、程序不为说。”①对行政不作为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也有多争论,有认为是行政不作为即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也有认为行政不作为只可能是违法的。笔者认为,研究行政不作为的合法违法性,必须依靠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而研究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就必须依靠研究行政行为的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的分类标准。分类决定各类概念从而决定其合法违法性。
二、对行政不作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词义分析首先,对于行政行为的分类有很多,这里列举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以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可以分为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行政行为以行政主体对行政法规范的适用有无灵活性为标准,可以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还有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等,”②还有与笔者所写论文有直接联系的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笔者之所以进行了列举是想说明,通过观察上述分类的名称会发现,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的时候,姜明安主编的这本书中的分类,都是在行政行为前面加上凸显分类标准的修饰词。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就像对人进行分类分为男人女人。而不是人男和人女。而这种类似于人男和人女的用词手法就是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的用词手法。这种现象在目前有关行政不作为性质的研究文章中,出现的非常多。如周佑勇的《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周佑勇《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中写道“法律行为按其方式不同,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与之相对,行政行为也因其方式不同有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之分。”③由这句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先区分法律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在加上修饰词行政行为。那么进行类推,笔者也可以先进行法律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区分,再加上修饰词民法行为,民事诉讼法行为,刑法行为,变成民法不作为,民法作为等。通过比较姜明安和周佑勇的分类,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站在同样领域内的,前者是以行政行为为基础,后者是以法律不作为行为与法律作为行为为基础。笔者认为在研究行政法领域的时候,理应当以行政行为为基础。理由有一下几点,首先这样研究起来会更直接。目前很多行政法的教材编排上都是,先研究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在研究行政行为的分类。也就是说目前的都是以行政行为为基础来研究行政行为的分类。其次对于周佑勇的分类,应该说是非常的新颖,但是目前并没有民法不作为,民诉不作为,刑法不作为等的研究,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最后,周佑勇的分类方法是对法律行为的分类后的再分类。“法律行为有很多分类标准,如根据主体性质和特点分为个人、集体、国家行为,单方行为与多方行为,根据行为的表现形式与相互关系分为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即作为与不作为。”④再在此基础上再分类的化,显得过于复杂。所以综上所述,我不赞成行政不作为的提法。因为这样会对行政法研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很多学者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也是以行政行为依据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学者必须在用词上将行政不作为纠正成不作为行政行为,这样才不会与以法律作为和法律不作为为基础的行政不作为混淆不清。同时也更符合我国的用语习惯,如前面我所提到的对人的分类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人男和人女。三、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下面具体来研究姜明安教授主编书中不作为行政行为和作为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和周佑勇教授文章中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中的分类标准。(一)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的分类标准前者的“分类标准是以是否改变现有法律状态(权利义务关系)为标准,可以分为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前者是指行政主体积极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和颁发许可证等。后者是指维持现有法律状态或者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政行为,如不予答复和拒绝颁发许可证等。”⑤即一个行政行为导致一个法律状态变动就是作为的。一个行政行为没有改变法律状态的就是不作为的。接下来,判断一下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合法违法性。按照标准,行为导致状态变是作为,行为导致状态不变是不作为。对于前者有两种可能,应变且变了(合法)不应变但变了(违法)。对于后者也有两种可能,应变但没变(违法)不应变且没变(合法),即不论作为行政行为还是不作为行政行为既有合法也有违法可能。那么现在来分析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例举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第十一条第五款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不予答复和拒绝履行按照上面对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因为两者都没有改变原来的状态,所以都是不作为的行政行为,那么就有可能是合法的或者是违法的,而合法违法只需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和拒绝这两个词在意思上都表示否定,所以往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种行为不对。但其实虽然两个词是有否定意思但并不代表违法的意思。并且虽然这两种行为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受案范围并不代表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违不违法是由法院进行判断的。(二)周佑勇教授的文章――《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中的分类标准周佑勇教授的分类标准是以行为的表现方式来区分作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行政作为是行政主体以积极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只要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了肯定或否定的明确意思表示或者实施了一定的动作行为,即可认定行政作为的形成。而行政不作为是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表现出来,无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外在动作行为。简单说就是有意思表示或动作则是作为,没意思表示或没动作就是不作为。接下来判断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合法违法性,对于第一种,有两种情况,应有意思表示或动作且有或动(合法),不应有但有或动(违法)。对于第二种,也有两种情况,应有或动但没有或动(违法),不应有或动且没有或动(合法)。这样看来按照周佑勇的分类标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两者都有合法或违法可能。但是,周佑勇在他的文章中对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进行了规定,“一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二是程序上表现为消极地有所不为,即没有履行该作为的法定义务。既有程序上的特点――消极的不作出或没有完成一定的程序行为;也有实体上的特征――不履行作为的法定义务。”⑥(周佑勇教授的观点是“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并重。行政实体的内容是通过行政程序来实现的。如果行政主体在程序上是消极地“不为”,那么在实体内容上可定就是什么也没做,因而它只能是一种行政不作为。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程序上积极的“为”,那么它反映的实体内容则可能是“为”也可能是“不为”即程序行为没动,则实体行为不可能动,则是行政不作为。程序行为动,实体行为可能动也可能不动。并且其又认为程序动了,不管实体有没有动就是作为,即程序动没动决定行政作为还是不作为”⑦)。简单说他对行政不作为构成的规定是,应当动但是没动(违法)。但是并没有规定应当不动且没动(合法)。因此其认为行政不作为就是违法的,判断了什么是行政不作为就可以判断什么是违法的,因此他会规定,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由此来判断什么是行政不作为。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和对行政不作为构成的规定,来分析一下不予答复和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是一种程序上没动,实体上也没动的行政行为,因此是行政不作为,因此是违法的,拒绝履行,是一种程序上动了,实体可能动也可能没动的行政行为,因此是行政作为因此可能是合法也可能是违法。但是《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可以完全上面的推断。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规定中的逾期未决定就是不予答复,但他并不是违法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行政不作为构成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笔者猜想之所以他认为应当不动且没动的行政行为不是行政不作为,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负有消极义务的人有所为,那么这种“不为”也不是一种法律上的行为,而只是一种遵守禁令的客观事实。”⑧也是说他认为法律规定应当不动且不动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行为。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首先我想说,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是一个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⑨对于这种遵守法律的行为使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也许有人会说,遵守法律,也许会使原来的状态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并没有产生、变更和消灭,因此不是法律事实。如我遵守法律不去偷盗你的东西,东西是你的这种状态是没改变。但是因为我遵守法律,这种生活状态已经产生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状态,要知道并不是生活中所有的状态都会成为法律状态,比如说我喝了一杯水,这种状态虽然改变,但不是法律状态,因此也不是法律事实。所以只要是遵守法律的行为,此行为无论是动的还是不动的,都是法律事实。其次我想说,法律事实分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法律行为是因人的意志而做出的行为,从而改变法律关系。法律事件是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从而改变法律关系,如一个人的出生死亡。因此,那种遵守法律规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周佑勇将它排除在不作为的法律行为外是不正确的。行政不作为是包括应该不动且不动,应该不动但动的。综上,我认为周佑勇对行政作为与不作为的分类标准是正确的,但将遵守法律消极义务的不作为视为客观事实,排除在行政不作为之外是错误的,并且因为只认为违反积极义务的不作为行为是行政不作为而推断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也是不正确的。不可能通过判断行政行为是不作为的从而判断其是违法的。四、对姜明安教授,周佑勇教授分类标准的评析评析一下,姜明安教授,周佑勇教授关于不作为行政行为和作为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作为的分类标准。(一)对姜明安教授分类标准的评析前者是以行政行为是否改变法律状态为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但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笔者认为分类的标准应该直接着眼于行为的动和静,而不是着眼于因行为动静而导致的状态动静。因为这是不必然导致的,姜明安认为作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积极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和颁发许可证等。但他没有考虑到行政主体为了积极改变现有法律状态,作出了行为,但是法律状态并没有改变的情况。而此时的积极行为应该是什么呢,难道是不作为行政行为吗?他认为的不作为行政行为是指维持现有法律状态或者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政行为,如不予答复和拒绝颁发许可证等,由此看到不作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维持和不改变状态。因此这种情况是不能规定到行政不作为的。因此这个分类标准显然缺少了行为目的是改变法律状态的行为,但是没有却没有改变成。之所以会有这种缺失,是因为,这个分类标准,是建立在行为动必然会导致状态动,行为静必然会导致状态静,前者不尽然,后者却是对的。也许有人会质疑,根本不存在行政行为是积极的而法律状态是静止的情况,或者说即使有,如行政机关征收拆迁房子,最后没有拆迁成,且不了了之,这种状况是可以忽略的,因为被征收方肯定不会去行政机关。但是笔者想说,如果这个房子的征收与否不仅影响到房主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影响其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也许是因为这个房子不及时拆除的原因,而给自己生活带来极不便利的相邻建筑的户主,也许是因为这个房子不及时拆除,而经过竞标已获得此块地皮的土地使用权,准别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开发商。他们都是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关人,完全有可能对行政机关征收拆迁房子最后没拆迁成进行,那么若认为这种行为,既不是作为行政行为也不是不作为行政行为,那么他还是行政行为吗,法院会以此为由拒绝受理吗?因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他不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分类标准并不完美,他假设行为动静必然导致状态动静是错误的,他忽略了积极的行政行为确没有导致法律状态发生改变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在原来的分类标准上在加上一条积极作为但没改变法律状态的行为,它的合法性违法性是看它到底符不符合法律。
(二)对周佑勇教授分类标准的评析周佑勇教授关于行政作为不不作为的分类标准是以行为的表现方式来区分作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我赞成这种分类因为他是直接着眼于行为的动静。因为作的动词意思就是“动”,若当成形容词则是“动的”,当他修饰行为时,就是“动的行为”所以区分作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理应当着眼于行为的动静,而不是因行为影响的状态动静或其他别的。但是对于周佑勇教授的这种分类,上面我已经提到过,缺陷就是认为因为遵守消极义务的消极的行为(静的行为)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行政不作为。因为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因此我建议将此类行为归于行政不作为。
五、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概念经过对以上两种分类标准的完善,笔者认为依据姜明安教授的标准,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概念是,行政主体以维持或者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为目的,而做出的维持现有法律状态或者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消极(静态)行政行为。依据周佑勇教授的标准,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概念是行政主体以消极的(静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行为,此行为既可能是履行法律规定的消极义务,也可能是不履行法律规定的积极义务。另外笔者想再强调一下就是,笔者仍建议将行政不作为这个词语用不作为行政行为来代替,这样才不会造成混乱,并保证行政法学研究中相关概念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林强:浅析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及构成要件[J],法制与社会,2007年8月。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3]周佑勇:《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J],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篇(5)
【关键词】行政处分 民事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 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一、问题与进路
在大陆法系民法体系中,法律行为( rechtgeschaefte )是与法定主义体系相并列的独特的设权行为规则。作为观念抽象,它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领域。它被誉为“民法规则理论化之象征”、“民法学辉煌的成就(the proudest achievement)”, 1其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民法自身的范围,而达至于行政法。Www.133229.cOM在德国行政法上,深受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影响的是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2这个产生于自由主义法治国背景下法概念一直是传统行政法的核心概念。3在法律技术层面上,民事法律行为对行政处分概念的塑型、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之核心要素被行政处分所吸收,行政处分因而被称为“行政法律行为”,4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发生分殊最终形成行政法上别具特色的“法的行为”( rechtsakt)概念,以及在晚近“基本法时代”、“行政国家”的背景下,行政处分概念又发生向传统民事法律行为回归等新趋势——在行政处分概念的发展、演化脉络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影响可谓若影随行。
深受德国行政法影响的中国大陆行政法亦设置了在功能上类似于行政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但是,由于对德国行政法上行政处分概念之形成、发展脉络以及其与民事法律行为之传承关系的缺乏了解,大陆行政法在借鉴行政处分概念以建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混沌状态。许多学者往往从各自所欲的立场出发,“创造、发明”形式各异的法律行为理论、行政行为理论,忽视了对学术传统的继受。例如,有学者认为,“从法学基本理论上讲,行为一旦受法律调整,它就能产生法律效果,它就应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事实行为”,所以,行政机关的行为只要受法律调整,具有法律意义,都是行政法律行为5。这种观点完全否弃了滥觞于罗马法的法律行为传统,将所有受到法律拘束的行为均纳入法律行为的范畴,亦否定了在当下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发挥支柱功能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对理论和实务均无益处。6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一个学术脉络——就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形成、发展之影响,以及晚近行政处分概念向传统民事法律行为回归等发展趋势作一个梳理与评述,以期对国内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相关研究产生一些“正本清源”的作用。
在方法上,本文将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概念与原则的关系之角度展开分析与评述。从法体系的角度观察,无论是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还是行政处分概念,它们分别是民法体系、行政法体系中“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所谓“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是指介于法的“内部体系”(法律原则构成的“开放体系”)与法的“外部体系”(抽象概念、类型构成的操作性体系)之间的“联系桥梁”,7它们是具有“目的性”和“技术性”功能双重属性的概念。就其“目的性”功能而言,它们并非为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涵摄”而建构,而是为了实现特定法律原则的功能,将其内容或价值包含并与之形成“意义关联”,8在适用过程中如有疑义,则应“回归”到它所包含的法律评价(法律原则)以取得符合规范目的的答案。其“技术性”功能则体现为以“建构类型”9的方法,在法的“外部体系”中进一步具体化为富有操作意义的“技术性”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它们是法律体系中纯粹的“技术性装置”,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在不同的法律领域所发挥的“技术性”功能,受制于它们与法律原则之间发生的意义关联。因此,作为“规定功能概念”的法律行为,可以在民法领域中成为实现“私法自治”原则的手段,也可以在行政法领域中实现“依法行政”等上位原则所蕴涵的价值。随着部门法的发展,法律原则可能产生新的价值导向,并与“规定功能法概念”之间形成某种新的意义关联,这个概念所发挥的技术性功能也会随之作出调整。
二、作为法律行为的行政处分概念之建构及其正当性
在奥托.麦耶的大作《德国行政法》中,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首次被界定为:“行政机关于个别事件中,规定何者为法,而对人民所为具有公权力之宣示”。10这一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行政法学获得学术上的真正自恰性,从规范性研究(正当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两方面脱离了国法学、行政学的“樊篱”,为纯粹“法学方法”(die juristische methode)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提供了契机。在政府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自由法治国阶段,行政法的绝对原则乃“依法行政”原则,它要求从规范性依据、运作结果等方面对行政权实施控制。由于政府职能较为简单,行政活动的方式也极为单一,行政处分被认为是当时国家行政最主要、最明显的活动方式。因此,行政处分概念成为承载“依法行政”原则之功能的最佳选择。11这个原则要求行政处分必须成为“合法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国家活动。此外,行政处分还必须是一个高度“形式化”、蕴涵“技术化”可能性的概念,以显示处于初创时期的行政法学不同于行政学、管理学、国法学等学科对行政活动的认识,并以行政处分概念为主干建构一套与民法体系相对应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12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深受理性主义法学和潘德克顿法学影响的民法学已斑斓成熟。在此背景之下,德国的行政法学者借助经典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来构建行政处分概念。
1910年柯俄曼(kormann)发表的《国家法律行为之制度》一书,标志着行政处分理论的成熟,他引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效意思表示观念,将私法行为与事实行为,以及公证、通知等准法律行为排除在行政处分之外,而仅视国家机关、公共团体所为具有法效意思的行为,为固有的行政处分。柯俄曼认为,行政处分是富有法律行为性质的国家行为,这种国家机关的法律行为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并无差异。国家机关的行为属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或公法上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并差异,仅视其是以私法上的权利主体或以公法上的权力主体而作意思表示为区分。但是柯俄曼将法院判决看作行政处分。柯俄曼的理论引起了众多德国学者的共鸣,其法效意思表示说奠定了传统德国行政法行政处分概念的基础。后来,学者f1elner在继承柯俄曼理论的前提下,将非行政机关所为之行为,如法院判决等排除于行政处分概念之外,使行政处分概念在学理上基本成型。13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之建构即以此为基点,完全照搬民法上的“法效意思说”。鉴于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大多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决定,德国行政法模仿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之定义,将行政处分界定为,依行政机关单方之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处分亦被认为是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14按照这个理论,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则被定义为依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如行政机关报工作人员在执行人务过程中殴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并不是依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而生,而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产生,因此系事实行为。再如,所有的行政执行行为(包括强制执行),其法律效果皆由前一个行政处分而生(执行的依据),执行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依据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因此,行政执行行为是事实行为。另外,还存在着行政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分类,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也由法律直接规定,但在准法律行为中,也有行政机关的表意,只是这种表意是效果意思以外的行政机关的意思、认识判断等表示作为(即不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因此准法律行为又称为观念表示行为。行政法上的观念表示行为大致上包括警告、劝告、确认、证明、通知、受理等形式。15
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建构的行政处分概念基本上可以满足自由法治国时期“依法行政”原则功能的实现。首先,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行政处分概念在行政法“外部体系”中,通过“类型建构”进一步区分为各种行政处分的“具体类型”(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等),形成一系列具有明确构成要件和法效果的“技术性概念”,从而便于对行政权实施控制和监管。另一方面,传统行政法上“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权的控制要点在于“事后控制”——即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权的运作结果进行司法审查,因此,作为行政权主要运作方式的行政处分便成为了进入行政诉讼 “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行政诉讼的主要任务在于审查行政处分的合法性。为了尽可能地实现这一功能,运用“推定式拟制”等法律技术的对行政处分概念的涵盖范围作扩张性的解释以扩大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也是传统行政处分概念的重要特征。所谓“推定式拟制”,是指那些“当事人并未有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并不明确的案型,基于规范上的要求,拟制有某种意思表示之存在;或将不明确之意思表示,拟制为有特定之内容”,这种技术具有“不得以反证推翻之推定”的性质。16“推定式拟制”主要针对“行政不作为”之案型,若行政相对人依法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其合法权益或许可其从事某行为,行政机关保持缄默或不予答复,如果按照意思表示理论解释,则行政机关并未作出行政处分,对这种“不作为”行政相对人不得提起诉讼救济,实与“依法行政”原则之规范宗旨不符。因此,在这类案型中,行政机关未明确作出意思表示被拟制为作出了否定性的意思表示,行政处分因被拟制而成立。17
然而,行政处分概念的建构却遭到了一些德国学者的反对和质疑。按照民法学的通说,法律行为乃民法领域实践“私法自治”原则的主要手段。18“私法自治”是民法体系中高位阶的根本性原则,其主要精神在于“个人自主”和“自我负责”。19为了实现“私法自治”原则的功能,立法者通过法律行为赋予行为人以意思表示创设、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并在民法“外部体系”中建构类型化的契约以及遗嘱、婚姻等与法定主义体系相并列的设权行为规则(具体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而形成了民法体系化之主干。魏玛时代的著名公法学家jellinek(耶里内克)就以此为依据,反对将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等同于公权力的意思表示。他认为,以民法上的营利业务(geschaeft)20来说明行使公权力并不妥当,尤其质疑将警察处理、征收处理与征税处理等视为法律行为。此后一直有学者反对以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来说明公法上的行政处分。21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民法学者werner flume(弗卢梅)的观点,他认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通常需要复数的法律行为共同作用而形成,而公法上的法律关系通常都是通过单方行为而形成,因此行政处分并非(民法上所称的)法律行为;民法上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体现,而行政处分形成的法律关系通常是单方要求相对人必须接受,其正当性直接来自于法律而非私人意思,并且需要遵循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处分虽然也与民法上法律行为一样具有目的指向性,但这是法律的要求,而非受制于行政的意思要素(willensmoment)。当具备一定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存在时,公务员即应作出一定行政处理,其在此并无创造性以及合乎自我意思的形成空间;行政机关的主观要素有时也具有重要性,例如在行政机关具有裁量空间时。但这与民法上法律行为中的自我决定仍有不同。因为行政裁量并非自由裁量,尽管在裁量范围内公务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但必须进行合义务的裁量并要以实现公益为目的,否则将构成裁量瑕疵。22
尽管遭受强烈质疑,但作为法律行为的行政处分概念仍然为学界和实务所接受。在司法实务中,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均形成了与行政处分相适应的诉讼类型。例如,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行政处分适用“撤销诉讼”,撤销即含有“撤销因意思表示所生之法律效力”之意;对于因行政机关不作为“拟制”而成的行政处分,适用“请求处分诉讼”;认为行政处分无效则适用“确认诉讼”;23
从现代法律方法的角度考察,早年德国学者引介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创设行政处分概念,以之作为行政法体系化的核心概念,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司法实务上均具有正当性和自恰性。民法领域中作为“私法自治”手段的法律行为,乃是“规定功能法概念”的“目的性”特征的表现。在“私法自治”原则的引领下,法律行为可以在法的“外部体系”中层层递进为契约类型、婚姻、遗嘱等各种具体的、可辨识的法律行为,为人的“工具理性”行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决定赋予法律上的意义和保障,进而成为实现“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工具。24但如果过于强调这一点则可能忽视了法律行为“价值中立”的“技术性”功能。法律行为“技术性功能”的本质在于授予行为人 “能力”或“权力”,行为人因而可以为自己或他人创设某种法律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涉及任何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法律行为仅仅是一种法律调整技术,目的在于弥补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的不足,25它与“私法自治”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以概念的精确分析见长的分析实证法学(analytical positivism jurisprudence)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
在美国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hohfeld)的权利的法律关系理论中,法律行为在逻辑上属于“power----liability”之法律关系,他认为,所谓power就是指a与b之间存在一种法律关系,a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创设a与b或b与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liability就是指b应当承受a通过自己行为所创设的a与b之间或b与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这种power被授予政府官员时,它是公法性质的权力,但它也可以是私法性质的,在私法领域,决定他人法律关系的power通常称为“authority”,而决定自己的法律关系的权力通常称为“capacity”。政府官员的所谓“权力”,其本质就是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创设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霍菲尔德认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的变化可以由两种事实产生:一是为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事实,二是为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事实。而power就是通过第二种事实来实现的。26在法律规范层面上, power就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代宗师哈特的规则理论则更为清晰地阐释了法律行为的这一特征。哈特认为,设定义务只是法律的任务之一,法律的另一个任务在于赋予“权力”,它使得人们能够在某些情况下自愿地实现法律关系的变化。哈特从而将法律规则分为设定义务的规则(第一性规则)与授权的规则(第二性规定)。前者是法律直接以“命令性语句”规定人们必须干什么、不得干什么;后者是法律并不直接规定,而是授权人们通过自己的意愿创设规则。27当“第一性规则”(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无法将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技术环节作充分的详细概括时,法律便以“第二性规则”授权人们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实现法律关系具体内容的确定化。因而,作为“第二性规则”重要机制的法律行为就起到了弥补法定主义调整方式不足的功能。应该看到,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法律行为)不仅有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或官方性质的,“这种权力在司法、立法和行政这三个部门到处可见。”28
就行政法而言,“依法行政”基本原则决定了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能否定法律行为(授权主义)调整方式在行政法上的自恰性。“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权的控制和监管并不意味着行政权运作的机械和僵化。行政关系的变动不拘、驳杂多样使得法律不可能对所有行政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法定主义方式无法使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这就为法律行为制度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行政处分(行政法律行为)在此起到了“桥梁”或“中介”作用,它通过行政权力的作用将抽象的、一般的行政法规范确定为特定个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行政权的作用则是通过“意思表示”创设法律效果,“意思表示”意味着“选择空间”的存在。在行政法上,行政权力意思表示的“选择空间”被称为行政裁量。裁量的本意是判断、决定过程中的自主性(autonomy)。当然,行政裁量并非“自由裁量”,其自主性远不如体现“意思自治”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行政”原则所包含的“权力行使之比例原则”对行政机关裁量选择(意思表示)作出了严格的控制,它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作出意思表示(裁量选择)时,不得背离决定的目的、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不得违反可行性原则、不得违反均衡原则、不得违反平等对待原则、不得违反惯例原则等,否则将构成裁量瑕疵,29但这并不能全盘否定行政机关“意思表示”形成法律效果的“创造空间”。正如台湾学者翁岳生所言,“裁量乃裁度推量之意”,虽然它“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准据和目标,因此和毫无准则限制之恣意不同”,但“行政裁量之斟酌衡量亦不受呆板之逻辑法则之约束,而在国家行政目的之大前提下,得有较大意思活动之自由。”30正是这种“意思活动的自由”使得行政处分所创设的法律效果并非单纯地依据法律,而是由其根据个案的情形选择、判断所定。
如果说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体现了民法“个人自治”的精神,那么,行政法上公权力的意思表示体现的则是“他治”,31即法律承认行政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律的范围内)单方面地为他人设定权利义务,用麦耶的话来说,是行政机关“在个案中规定何者为法之宣示”。这就是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法律行为,在行政法上表现出的与民法法律行为迥然不同的“目的性”特征。
三、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分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强人权保障的呼声日高,欧陆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出现了“打开诉讼之门”、扩大人民诉权的发展趋势。但当时西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均以行政处分作为进入“行政诉讼通道”的前提条件。经由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锤炼而成的行政处分概念尽管十分精致,但其涵盖的范围却十分有限。按照传统的行政处分(法律行为)理论,行政法上所有的执行性行为均属事实行为,32即使是行政强制执行、即时强制这类极易侵害人民权益的行为亦被视为是事实行为而不得提起诉讼。而包含行政机关意思、认识判断等表示作用的准法律行为,由于其法律效果非依意思表示产生也被排除于诉讼范围之外。行政处分概念仅指依照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大量的不含有意思表示作用,但实际上对人民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人民均不得对之提起诉讼,司法权亦不得予以审查,这种状态显然与新形势下“依法行政”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的要求相悖离。
在这个背景下,对传统行政处分概念的批判逐渐成为潮流。上个世纪 60、70年代,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司法实务界出现了拒绝采纳传统学说的趋势,同时尝试对这个“规定功能法概念”之“技术性”功能作出调整,进而形成了新的有关行政处分之理论。台湾学者称其为“客观意思”说。33该学说认为,“法律行为之行政行为,并非完全依表意人之意思为凭,而常须受表示于外部之客观形态或法令支配。”因此,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皆应依其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果为断”,34是否于行政相对人产生拘束为准。这种行政处分理论基本上否定了援引自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表示”,全然不顾行政机关行为的主观意图,而仅以行为客观上的拘束、规制效果为判断标准。以传统理论标准划分出来的事实行为或是准法律行为,只要在客观上对特定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了直接规制或拘束,即可视为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处分),从而极大地扩张了行政处分的适用范围,拓展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通道”。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可以视为作为“规定功能概念”之法律行为,在“依法行政”原则要求强化司法审查的价值导向下所作出的调适。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新的行政法律行为理论已与行政机关的“内心意思”无所关联,但并未完全截断行政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衔接,新的理论被称为“客观意思”。“客观”一词在语义上具有“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之涵义,而“意思”一词是指人的“内心意愿”。35 “客观”与“意思”的组合在语义上看似矛盾,实际上意味着“意思推定”的作用,即凭行政机关外在的客观的行为效果推定出其主观的意思表示。新的行政法律行为理论认为,并非在每一个行政法律行为中,均有行政机关意思表示的作用,如传统理论认为是事实行为的行政活动,只要在客观上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了拘束,即认为是行政处分,这种行为并非依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而此时仍然运用了“推定式拟制”的法律技术,即使行为人“无此类意思时亦被当作意思表示处理”。因此,“客观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拟制的意思表示,传统理论中的事实行为、准法律行为只要在客观上产生了法律效果,即被拟制为法律行为。按照这个理论,“客观意思”有可能成为行政法上特有的“意思表示”理论,它将行政法律行为与民法上经典法律行为理论在形式上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两者之间形式的联系并不能掩盖其实质的不同,因此,为了避免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aft)之概念相混淆,德国学者将行政法上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称为rechtsakt,有台湾学者将之译为“法的行为”。36
从“法效意思表示”转变为“客观意思”的行政法律行为,其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也导致行政处分概念与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分殊。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按照“客观意思”认定行政处分(法律行为或法的行为)的存在“着重只是法律效果的有无,至若实际行为态样是直接出自人力的文书、标志、符号、口头、手势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乃至非直接由人力,而系由号志与电脑等自动化装置作成的表示,在所不问。”37
由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深厚影响,新的理论并未被学界所一致认同。但它在司法实务上却产生了重大的反响。1976年制定的德国现行《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处分所作的定义是:“行政机关在公法领域中,为规制个别事件,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所作的各种处置、决定或其他公法措施。”这一定义强调了行政处分的“规制”(regulate)效力,并且以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并不要求依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机制——根据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于90年代制定的“行政程序法”、“诉愿法”对行政处分的定义也强调其“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特征,并未采用“法效意思”说。38在德国行政法院、台湾地区“行政法院”的历年判例中,这种以“客观意思”为基础的行政处分概念亦得到了认同。39总之,扩张以后的行政处分概念虽然构成了对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离经叛道”,但在“技术性”功能上因应了“依法行政”原则加强司法审查、扩大人民诉权的要求。
我国大陆行政法学界虽未明确提出行政法律行为的建构理论,但在具体行政行为这个与行政处分有着类似功能的概念建构中,理论与实务均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客观意思”说,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这类行为并不一定都依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但在客观上均能产生法律产果,因此将其视为具体行政行为。40但是,如果我们在不了解“客观意思”说与民事法律行为源流关系的前提下,仍然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位为“行政法律行为”的话,就产生了理论上的混淆,从而在界定行政法上事实行为等问题时进一步陷入理论上的“乱麻”。不幸的是,这种混乱的局面已成为当下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之现状。我国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一般都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位为“法律行为”,强调其对外产生法律效果而不援用“法效意思表示”,这一做法与“客观意思”说趋于一致。但是,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具体阐释时,41或者界定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时,又会引用“意思表示”概念。这种前后矛盾的根源在于对行政法律行为学说史的忽视。
四、行政处分向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回归及其新趋势
如果说行政处分概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分殊乃是为了适应实践“依法行政”原则所不得不作出的调整,那么,随着基本法时代人权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在现代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语境下政府职能的多样化、行政活动的变化万端,以行政处分为核心概念建构的传统行政法体系则遭遇了空前的挑战,42行政处分概念在行政法上的架构和功能也面临着更大的变数。
首先,在行政诉讼法上,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行政诉讼制度普遍确立了“除宪法争议以外的一切公法争议”的受案范围。43行政诉讼程序不再以行政处分为“通道”,受案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行政处分只是影响诉讼类型而不涉及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为扩大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而建构的“客观意思”之行政处分已无存在必要。
其次,在现代行政国家,国家行政事务的重心已从传统的“干预行政”、“高权行政”转向“计划给付”和“要求行政”(forderungsverwaltung)。在德国,要求国家积极实施社会福利、追求实质正义的“社会法治国”之宪法原则亦逐渐成为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国家行政事务重心的改变,必然引起行政活动方式的转变。行政活动形式除了行政处分等传统的公法手段外,还要求利用私法方式平衡、直接控制与间接影响相配合等。契约式协商、信息和指示等新的行政活动形式越来越占据显著的地位。44显然,行政处分在行政法中的核心概念地位受到了挑战。
另外,行政处分的“静态”和“缺乏弹性”之特征使得它在很多情形中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变动不拘、驳杂多样的行政现象。传统的行政处分方式主要关注行政过程的终点,对行政权运行的结果实施控制。但现代行政必须面对各种高度技术性的事项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这要求行政机关在整个行政过程中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政策目标,必须进行环环相扣的不同行政活动形式的链接与耦合,将政策、政治和法律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变量,对行政过程中的实体性因素予以分析和判断。45传统的行政处分活动方式只是“静态”地将法律看作是一个预设的常量,缺乏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另外,行政处分以行政机关单方面创设法律效果为特征,这种法律效果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但随着时间的经过,行政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往往使得行政处分的法律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行政处分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僵硬性”。
在 “基本法时代”、“行政国家”的背景下,以行政处分为支柱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已显得捉襟见肘。关注行政过程、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政策考量、风险规制等实体性因素成为近来行政法学研究的潮流。尽管这些新的研究动向尚未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行政法的理论架构,但在行政法教义学中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的行政处分亦应作出“技术性”调整,力求在法拘束的明确性(依法行政原则)与法适应性(社会法治国原则追求实质正义的要求)之间作出平衡,以克服传统行政作用方式的“僵硬性”。
近年来,在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上,以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来定位行政处分概念成为新的趋势,行政处分概念又回归到民事法律行为“法效意思表示”理论。正如德国学者毛雷尔所言:在基本法时代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已经超过了行政处分的范围,因此应更多考虑概念本身的逻辑性,46导致行政处分向传统理论回归的重要原因乃是由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基于扩大诉讼救济范围之功能主义考量而建构的“客观意思”说已无用武之地,用“法效意思”解释行政处分可以和根深蒂固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保持一致,从而避免与传统理论“离经叛道”产生的理论风险。在司法实务上,亦倾向于用“意思表示”来解释实定法上的行政处分概念,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上行政处分定义中的“规制”被解释为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规制的实质即为意思表示,只有通过引入规制或者意思表示的要素,才能将行政处分与行政上的事实行为(realakte)区分开来。47用传统理论来解释行政处分概念将引起行政处分涵盖范围的缩小,这与实体法上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行政处分已失去昔日绝对核心概念之地位不无关系。
另外,为赋予行政处分概念“弹性”和“适应性”,将原来作为最终决定的行政处分予以“分节化”、“时间序列化”,灵活运用行政处分的附款成为新近的制度设置。例如,利用“部分决定”或“预备许可”制度,使一个完整的行政处分得以多阶段化,以应对事实变化的可能性以及行政规划、行政相对人生活安排的连续性要求。这种制度设计创设了具有变化潜能的行政处分的中间形态,从而提高了行政处分的“适应性”。而灵活运用行政处分的附款,允许行政机关事后修正、更新行政处分则使行政处分获得“弹性”。总之,晚近出现的各种行政处分新的制度设计,尤其是行政处分中间形态的精致化,一方面试图克服传统行政处分可能衍生的僵化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行政处分所具有的促成法的安定性、类型化等重要功能。
篇(6)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125-08
关键词:意思表示错误;法律行为;行为人;表意人;比较法学;私法;民法通则;合同法
Abstract: Declaration of the inten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legal acts,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act as a fundamental factor. When there is an error in effect meaning or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tent, the effect of corresponding legal acts will therefore produce certain effect. With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legal acts of wrongly expressed meaning,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has a regulation that it is revocable or invalid. In addition, it is considered effective occasionally by interpretation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of legal acts and protect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s, our future civil code should in principle rules that the effect of legal acts of wrongly expressed meaning is revocable, meanwhile, we ensure that the civil code prioritiz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 to judge its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declaration with wrong intent; legal acts; actor; representor; comparative law; private law;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Contract Law
一、引言
意思表示乃法律行为之本质属性,是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最根本因素,当一项意思表示完全有效时,如果不考虑法律行为有效的其他因素①,那么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法律行为当然有效。但是当一项意思表示出现瑕疵时,法律行为的效力到底是有效,无效抑或可撤销呢?对此恐怕需要根据不同情形做出不同回答。在传统民法学中,意思表示错误属于典型的意思表示瑕疵,乃意思与表示无意不一致的情形②。关于其效力,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虽然对其有所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分歧,并非尽善尽美。我国只是有关学者提出的民法总则建议稿对其加以提及,而在现有立法中却没有相关规定。鉴于此,笔者针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情形,拟采比较法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并同时通过引入意思表示解释理论对其效力给出更富弹性的答案,以期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一般原理
(一)意思表示的内涵
根据当今德国学界的通说,“意思表示”这个概念是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的“承诺拘束理论”(Theorie vom verbindlichen Versprechen)演化而来的③,就立法而言,意思表示首次在1794年被规定在《普鲁士普通邦法》中,从而开启了将“意思表示”纳入法典编纂之先河。并且,该法还进一步规定:“所谓意思表示,是应该发生某事或者不发生某事的意图的客观表达。”〔1〕这种对意思表示的具体定义尽管在后期颁行的各国民法典中再也无法找到,但是学者们对其给出的定义却是目不暇接,而且表述也多相类似。如我国大陆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认为,所谓意思表示,指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的行为〔2〕;我国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意思表示是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3〕;日本学者山本敬三认为,所谓意思表示,是表示――令一定的、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发生的――意思的行为〔4〕;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茨认为,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的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点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生并产生效力〔5〕。由此可见,意思表示(Willenserklrung)就是一个行为人将其内在意思向外界表示出来从而产生一定私法效果的行为。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界定
在传统民法中,意思表示由内部意思和外部表示组成。内部意思包括行为意思、表示意思和效果意思〔6〕,共同构成具体法律行为完全有效的必要主观要件。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出现了瑕疵,那么法律行为则会相应出现瑕疵,甚至根本无效。同理,外部表示作为构成具体法律行为完全有效的必要客观要件,如果出现瑕疵,亦会影响具体法律行为的效力。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就是指在主观要件或者客观要件方面出现了瑕疵,其导致了表意人在客观上通过其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与其内心的初衷意思不相吻合,产生了意思与表示偶然的不一致④。对意思表示错误的界定就是一个寻找所发生的瑕疵到底是出现在纯粹的意思阶段,还是出现在纯粹的表示阶段的过程?一旦我们找出了这两个阶段中的瑕疵,意思表示错误的问题就有了定论。
当意思表示错误出现在纯粹的意思阶段时,由于内心意思包括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与效果意思三个层面,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去找寻一番呢?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首先,行为意思完全不涉及某种法律上的意义,比如甲主动请他的同事乙吃饭,不管甲是真的想请,还是假的想请,法律都无法去干涉,也就是说在此种情况下,甲请乙吃饭只是一种纯粹的情谊行为,一旦甲并没有请乙吃饭时,法律对甲来说是无可奈何,对乙给不了任何的救济。换句话说,这里的意思表示是否错误完全触及不到法律行为的范畴,所以从分析法律行为的效力层面来看,不必要去考虑它⑤。其次,表示意思也同样不用考虑,因为表示意思也并不产生当事人之间某项具体法律行为的效果,不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某种具体的法律上的约束力。既然没有产生这种效果与约束力,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去考虑此时意思表示是否错误的问题。显然,在排除了对前面两个层面的考虑之后,现在只需要对效果意思这一子层面是否出现错误进行界定,不过分析问题并不是在用排除法做选择题。“意思表示错误”中的意思之所以应为效果意思,其理由在于根据意思表示主观要件来看,效果意思就是指表意人具有了意欲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内心意思。法律效果在表意人的心里到底怎么样只有通过效果意思来衡量,所以当这种效果意思出现错误时,才可能产生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况,从而发生法律行为之效力出现相应瑕疵的后果。比如表意人想把自己的某本法律教科书赠与给甲,而在赠与时他把另外一个人乙错误地当成了甲,显然他在为赠与时,其意欲发生赠与效果的特定对象就出现了错误,从而这种赠与之法律效果就产生了瑕疵。当意思表示错误出现在纯粹的表示阶段时,即为在对外的客观表示上出现了错误。比如表意人在向对方发出意思表示的时候,不小心在书写价格时发生了笔误,将200元误写成了2000元。不过由于实践中往往很难将对外客观表示上的错误同效果意思的错误区分开来,故传统民法将这两者在法律效果上一视同仁,并没有做出严格的区分〔7〕。
综上观之,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就是指在意思表示已经成立的前提下,要么其效果意思层面出现了错误,要么其客观表示层面出现了错误⑥。同时,因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所以一旦出现了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时,法律行为的效力也会随之出现瑕疵。由此可见,要想探讨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根本的前提工作就是从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这一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界定意思表示错误,从而找寻出相应情形下的法律行为之瑕疵,然后对其加以分析。
三、域外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的现行规定与评析
德国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诺瓦里斯有句名言:“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克茨教授更是有云:“作为一位法律家,也只有具备有关外国法律制度的知识,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法律。”〔8〕我国当代的民法学大都是从欧洲大陆法系的模式上引进过来的,是西学东渐的标志性产物,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肯定,我国的民法学发展必然还将循此方向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要想彻底的弄清我国的民法理论,当然少不了将国内外的法律制度进行对比研究。笔者在此也尝试着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的立法例加以分析。
(一)德国民法的现行规定与评析
1.德国民法的现行规定
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和第120条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第119条规定了因错误而可撤销,其第1款规定,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就其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无意做出这一内容的表示的人,如果他在知道事情状况且合理地评价此情况时就不会做出该表示,则他可以撤销该表示;第2款规定,关于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视为关于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第120条规定了因误传而可撤销,为传达而使用的人或机构不实传达的意思表示,可以按照与根据第119条撤销错误地做出的意思表示相同的要件撤销之。
2.德国民法现行规定的评析
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其错误往往会因发生在意思表示在通往到达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经典的德国民法学著作将错误划分为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两大类,表示错误又进一步分为表示内容上的错误和表示行为上的错误〔9〕。德国民法典对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实际上也正是建立在与此相应的三个阶段之基础上:第一,在意思的形成阶段,表意人往往会对自己将要做出表示的理由及其相反的理由进行一番十分复杂的内心博弈,比如表意人在考虑购买一本书时,可能会思考:这本书在同类著作中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其对自己将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其性价比是否适宜?这些都是表意人做出意思表示的理由,如果表意人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错误,就是在意思形成阶段发生了错误,即动机错误。第二,在考虑如何将这一意思加以表示的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必须找出那些将这一意思以某种能为对方所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话语或者其他符号,比如表意人想把自己的某物赠与给其故友甲,而在赠与时他把另外一个人乙错误的当成了甲,显然他在为赠与时,把实际上的乙表示成了甲,这时就出现了内容错误,其往往包括标的物的同一性、相对人的同一性、价款、数量等因素的认识错误。第三,在将其决定使用的表示符号表达出来的阶段,也就是说他想把他的真意说出来或写出来,同样在上述的赠与例子中,他如果对赠与的对象没有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即赠与的对象确实是甲,但是在他表述出来的时候由于不特定的原因发生了笔误,将甲错写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就出现了表达错误,也即表意人实际使用的表意符号与其本来想使用的表意符号不一致〔10〕。
显然,并不是所有上述的错误类型都能成为使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疑问的原因,尤其是那种完全只是停留在意思形成阶段的动机错误往往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不生影响。否则的话,每一项法律行为都会受到一种不可承受的不稳定因素的侵扰,且与民法在一般情形下以保护交易安全为准则的理念相违背。从德国民法典对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来看,其包括内容错误与表达错误两种类型,而关于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情形所发生的错误,除了将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的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错误之外⑦,其它情形一概不属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范畴。另外,在德国民法学界也提出了一些归属不无疑问的错误,如法律效果错误、签名错误、计算错误等情形。这里同样可以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分析而得出其到底属于内容错误、表达错误抑或是一些民法典不予关心的错误。比如在法律效果发生错误的情形下,如果法律效果系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者,此时的法律效果错误为内容错误,表意人可以据此撤销其意思表示,如果法律效果系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者,此时的法律效果错误多为无关紧要的动机错误,表意人往往不得据此撤销之〔11〕。
无论是内容错误,还是表达错误,第119条都是硬性地规定这些情况下的法律行为是可以撤销的。即只要发生了内容错误或表达错误,表意人如果是非故意的做出错误的表示,那他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选择撤销其法律行为,从而使得开始有效的法律行为彻底地变成了无效。这样的规定果真完全合理吗?在笔者看来,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规定有三大不足之处,一是缺少弹性,不能很好地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交易。比如通过规范性解释发现,虽然所查明的意思与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不一致,但是如果前者对表意人更有利,那么表意人则不得撤销,因为错误人不应该因其错误表示而被置于更为不利的处境,他也没有理由通过撤销来消灭自己的表示⑧;二是对表意人可撤销的主观前提之规定仅限于非故意,并非合理。从该第119条的规定来,表意人除了故意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外,在其他情形下他都可以撤销,即使其具有重大过失也如此。这种规定过度保护了表意人可撤销的权利,未较好地兼顾到该法律行为相对人的履行利益,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撤销的前提应该以表意人不具有重大过失为宜⑨;三是将交易上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的错误一律视为内容错误,并非妥当。相反,应该将性质错误根据是否能从交易中加以推断而分为动机错误与内容错误,即性质错误在具体的交易行为中如果已经明示或者完全可以通过推定得知,那么就是内容错误,相反,如果性质错误在具体的交易行为中完全找不到丝毫的痕迹,那么就是动机错误。另外,德国民法典第120条所提及的是因误传而可撤销的情形⑩,其考虑到了表意人与受领人之间并不是直接互信,而可能是通过一个传达人作为媒介来互信,实乃周全,并且言简意赅地规定准用第119条,颇值肯定。
(二)日本民法的现行规定与评析
1.日本民法的现行规定
日本于1890年公布的旧民法被1896年和1897年公布的新民法取代后,一直施行到今天,这部民法是亚洲第一部完整的、直追法国、德国民法典的民法典B11。日本民法现行的规定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尤其是总则编的绝大部分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该民法典第95条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进行了规定,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的要素中有错误时,无效。但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表意人自己不能主张其无效。
2.日本民法现行规定的评析
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该民法典第95条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规定有较大差异。其表现有三:(1)该民法典第95条只是笼统地规定了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不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将意思表示错误明确地限定在内容错误与表达错误这两种情形。正因为这样,在日本民法学界对法律行为中的要素错误一直都存在错误二元论与错误一元论之争。二元论者认为该第95条所说的要素错误原则上只限于内容错误与表达错误,并且学界将这两种错误统称表示错误,至于动机错误原则上不予考虑,显然这种二元论者的观点实际上源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规定。一元论者认为,该第95条所说的要素错误不仅包括表示错误,还包括动机错误,其理由在于内容错误往往与重要的动机错误难以区分。相比较而言,明显二元论者的说法更符合民法在一般情形下以保护交易安全为准则的理念,因为按照一元论者的说法,在该第95条规定的前提下就会大量出现因错误而无效的情形,实不可取B12。(2)该民法典第95条仅规定法律行为要素错误的结果为无效,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的可撤销。该法第95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相比,更是缺乏弹性,这样硬性的规定没有给当事人留下丝毫事后选择的机会,所以即便当事人依然想让此法律行为完全有效,也必须重新达成法律行为,无疑为当事人的交易制造了麻烦,所以从立法价值上说,该法第95条当然不利于鼓励法律上的交易。(3)该民法典第95条规定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无效的主观前提是:须表意人没有重大过失。即当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他就不能主张无效,而不是仅仅在故意时才不能主张无效。该规定对无效情形的表意人之主观前提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更为合理,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除了这三大差异之外,日本民法典有些遗憾的是没有像德国民法典那样专门规定因误传而可撤销的情形。
(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现行规定与评析
1.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民法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民法,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民法,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采用了德国和瑞士民法的模式B13。该民法第88条和第89条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第88条规定了因错误而可撤销,其第1款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事情,非要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第2款规定,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若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第89条规定了因误传而可撤销,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传达不实者,得比照前条之规定,撤销之。
2.我国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的评析
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该民法第88条的规定基本上是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关于表意人撤销该法律行为的主观前提问题,该第88条第1款规定表意人可撤销的主观前提是表意人自己没有过失,这既不同于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没有故意,也不同于日本民法典规定的没有重大过失。那么关于该第88条中所谓的没有过失,到底应如何理解呢?换言之,是应解为没有重大过失?还是解为没有具体轻过失?抑或解为没有抽象轻过失呢?B14如果解为重大过失,往往会与法律文义不符,因为民法对重大过失一般都会特别指明,否则,就不应该当成重大过失来处理。但是如果解为具体轻过失,尤其是抽象轻过失时,显然表意人往往就很难有行使撤销权的机会,因为表意人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完全没有过失是比较少见的,相反,往往会有或多或少的过失成分。所以为了充分发挥该法第88条规定之宗旨,真正地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避免在具体解释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争议,似乎还是应该仿效日本民法典的立法例,将这里的没有过失明确规定为没有重大过失为宜。
在分析完因错误可以撤销的情形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接下来第89条所提及的是因误传而可撤销的情形,并且简洁规定准用第88条即可,其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如出一辙,完全值得肯定。
四、我国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一)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和《合同法》第54条虽然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做出了规定,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与上文中提及的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的规定相比,却较为薄弱,其不足之处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规定中只有“误解”,没有“错误”。从语义上看,“误解”的范围明显要窄于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中规定的“错误”,比如表意人在表达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显然就不能说成是误解,所以这里所说的误解充其量只是传统民法中规定的内容错误,而不包括表达错误。第二,《民法通则》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虽然大体上相当于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中规定的内容错误,但依然存在着差别。因为《民法通则》将误解用“重大”做了限定,也就是说只有在误解为重大时才考虑撤销该法律行为,而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的规定只要求对内容产生了错误就可以撤销,而没有将内容分为重大与不重大的情形。对比观之,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的规定较为合理,因为只要是作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无论其重要与否,双方当事人都必须达成合意才可能成立法律行为B15。第三,《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存在着不协调,单从《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它强调了误解的对象是对行为内容的错误认识,但是单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它只是笼统地说重大误解,而至于误解的对象是什么,没有规定。比方在意思形成阶段发生了误解,而其根本没有在合同中体现出来,此时发生的重大误解就往往不会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从而无需考虑该重大误解的情形。所以《民法通则》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较《合同法》更为合理B16。第四,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效力时,尽管在传统民法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基础上添加了可变更的规定,这样当事人就不用先撤销再重新达成法律行为,而是可以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变更即可,无疑为当事人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却依然没有引入意思表示解释具有优先性这一更富有弹性的规定B17。
(二)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规定的完善
1.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类型之效力的具体规定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为笼统,最缺乏弹性,德国民法典对错误类型的区分不够严谨,并且对撤销人的主观条件规定得不尽合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尽管对主观条件规定得相对合理一些,但仍不明确。为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在借鉴上述民法部分规定的基础上,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似乎应该更加具体地规定为:“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就其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无意做出这一内容的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该表示,但是如果表意人在做出意思表示时有重大过失的,不得撤销。”“当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已经明确或者可以推定地纳入法律行为之内容时,也当然是一种内容错误。”另外,关于因误传而可撤销的情形,应该效仿德国民法典,简洁规定其准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即可。
2.不同编章规定的协调性与简明性之遵守
一部法律的规定要想具有体系性,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做到前后立法的协调与简明,否则的话,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就更是无从谈起。从笔者在前文中对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的问题分析来看,《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重大误解的规定已经产生了不协调,并且《合同法》是在完全重复《民法通则》的规定。由于这种不协调与完全重复的规定将会给法典化带来极大的障碍,所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要严格杜绝之。况且,我们都知道法典编纂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法律关系进行分门别类,抽象出各种类型法律关系的共同规范,由此构成相对完整的规范体系〔12〕,特别是我国在依循潘德克顿法学派所创建的“总―分”模式来编纂民法典时,这将是一项更加精细的工作,它对协调性与简明性的要求,更是自不待言。
3.引入弹性规定的途径:明确意思表示解释优先原则
德国法儒萨维尼曾经说过,法律的开端和基础均来自对其本身的解释,法律的解释是一种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工作〔13〕。我们都知道,在以充分崇尚私法自治为核心的民法体系里,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表示所达成的法律行为即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所以解释法律行为与解释法律就显得同等的重要。法律行为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内心意思,二为对外表达。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无法清楚地表达于外部时,则有解释之必要。在对法律行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当无法获知当事人对表示的实际理解时,就有必要对针对法律行为加以规范性解释,即解释者把他自己置入意思表示受领者的情境中,了解意思表示的受领者在表示到达时已经认识或者可以认识的情境〔14〕。意思表示解释不仅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更具有优先性。下面就意思表示发生内容错误与表达错误的情形各举一例来详细地说明这一问题:
(1)关于内容错误的情形。1979年在德国哈瑙州法院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在该案中,一所女子中学的副校长为该所中学订购了“25罗卷”(25 Gros Rollen)卫生纸。客观上,罗(Gros)的意思为12打。因此,副校长订购的数量应为12×12×25卷(=3600卷),每卷1000张(判决书中写道,这一数量可以满足学校若干年的需求)。而副校长以为,“罗”(Gros)是一种包装方式的称呼,亦即她只想订购25卷B18。在本案中,作为受领人的纸厂这一方,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为一个理想人显然是可以察觉到对方要约中的卫生纸之数目多得不同寻常,所以最后双方在履行买纸合同而对其数目发生了纠纷时,就完全可以首先从效力宣示主义的意思解释标准出发来对数目多少进行定夺,从而使得该买卖卫生纸的法律行为在最终通过解释得出的数目上完全有效,而没有必要一概认定该买卖卫生纸的法律行为因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出现了错误而可撤销。这样一来,显然当事人就省去了先撤销此合同,再重新为法律行为的麻烦。相反,如果确实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得不出副校长的本意是只想订购25卷卫生纸的话,那么副校长再依据第119条撤销该法律行为也为迟不晚。
(2)关于表达错误的情形。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一句古谚:误载不害真意原则(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15〕。比如,甲与乙磋商后只愿意购买乙的A车,某日甲发出要约于乙时,由于在要约上发生了笔误,而将A写了B,乙知道甲的真意为购买A车,而为承诺时,此时双方当事人的买车合同到底效力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依据“误载不害真意原则”的解释方法,认为双方当事人关于A车的买卖达成完全有效的合同,不生错误的问题。
由此可知,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先行于意思表示错误时撤销规定的适用。简而言之,解释先行于撤销原则。所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除了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做出规定之外,还应该明确意思表示解释的优先原则B19。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构建一种私法效果的弹性机制和更好地完善我国民法体系。
五、结语
法律行为理论博大精深,其最终功能之体现在于充分实现私法自治,从而对行为人的行为发生法律规范的效力。探讨一项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通观本文之论述,无非是在假设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仅仅以意思表示错误为视角来探讨相应情形下的法律行为之效力。一方面,笔者在坚守传统民法对意思表示错误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述了错误的最终根源――即内心意思层面的效果意思或外部表示出现了错误,从而为分析此种情形下法律行为之效力上的瑕疵到底“瑕”在何处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在肯定传统民法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的规定之上,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成功与不足,最后结合我国民法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在立法上的缺陷给出自己的建议,但愿其能够为完善我国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之效力的规定有所裨益。
注释:
①法律行为的效力因素除了意思表示本身健全外,还包括当事人须有行为能力以及标的须可能、确定、适法、妥当。不过,关于标的是否须可能之问题,2002年修正后的德国新债权法认为一切类型的合同都可以以自始不能的给付为标的。详细内容可参见Medicus, 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C. H. Beck Verlag, München,2010, S.1。
②该情形又被称为无意识的非真意表示。详细分析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96页。
③米健教授认为这个术语最初的根源似乎见于中世纪晚期神学家们有关诺言和誓言的诠释之中,后来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其承诺拘束理论中提出了承诺的拘束力问题,并采用意愿表示概念来表达,最后在契约概念的法学理论中形成了意思表示这个下位概念。详细分析参见米健:《法以载道――比较法与民商法文汇》,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37-545页。
④其不同于意思与表示故意的不一致,在传统民法上,意思与表示故意的不一致指心意保留、戏谑表示与虚假行为。具体分析可参见Flume:Das Rechtsgeschft, 4.Aufl., Springer Verlag, Berlin, 1992, S.402-415。
⑤如果是在行为意思完全缺失的情形,意思表示则不成立,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没有必要去追问意思表示是否错误,因为对意思表示错误进行探讨之前提乃意思表示已经成立。
⑥当然,也不排除意思表示同时在意思阶段与表示阶段皆出现错误的情形,但该情形较为少见,况且,只要将上述两种情形都弄清楚了,那么在两个阶段都发生错误之情形的结果则不言而喻。
⑦该款规定是在民法典第二草案中被加进去的,当时立法者关于这一问题缺乏一种清晰的思路,今天德国的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一条失败的规定。请参见Kramer:Münchener kom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C. H. Beck Verlag, München,2007,§119 Rn.10,88。
⑧此种情形实际上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来排除撤销之可能。
⑨那么为什么不为具体的轻过失或者抽象的轻过失呢?因为如果解为具体轻过失,尤其是抽象轻过失时,显然表意人往往就很难有行使撤销权的机会,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后文的分析中还将提及到。当然即使表意人具有重过失,只要相对人明知的话,也一样可以撤销,并且撤销后对相对人不负信赖损害赔偿义务。
⑩关于传达错误的性质,德国民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将其视为表达错误的一种,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与表达错误并列的一种错误。参见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B11日本的旧民法是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谢怀蚶舷壬一直都很赞赏日本对西方法制的继受以及将继受而来的法律进行很好的“日本化”,他曾谓:“日本作为一个东方的封建国家,原来什么近代法律都没有,在10年内一变而与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并立,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对日本民法典详细地讨论参见谢怀颍骸洞舐椒ü家民法典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05页。
B12日本学界将错误二元论又分为信赖主义的错误二元论与合意主义的错误二元论,将错误一元论又分为信赖主义的错误一元论与合意主义的错误一元论。详细分析参见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35页。
B13梅仲协先生曾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诚巨制也。”参见谢怀颍骸洞舐椒ü家民法典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B14所谓重大过失,是指显然欠缺通常人之注意者,几乎接近于故意之程度;所谓具体轻过失,是指欠缺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之注意;所谓抽象轻过失,是指客观过失,其以一般人之注意能力作标准,台湾地区民法称之为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具体分析参见刘得宽:《民法总则.增订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页。
B15王泽鉴教授也认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必须同时具备必要之点的合意与非必要之点的合意。具体分析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B16或许有人会认为,尽管《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较《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的规定要宽泛,但它是在《民法通则》的总领性下适用的。尽管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在法律的具体适用时,往往是直接先考虑《合同法》的规定,此时就出现了《民法通则》失灵的问题。
B17德国民法典中虽未明确规定意思表示解释的优先性,但不少判例广泛运用了该原则。参见Brox,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6.Aufl., Franz Vahlen Verlag, München, 2012, S.64。
B18在德文中,gros(罗)与groB(大的)仅一字之差,而由于“罗”不是常用词,因此很容易被理解为“大的”。本案中,副校长即认为gros乃groB之意。参见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10, S.308。
B19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虽然规定了意思表示的解释,但其规定非常笼统,根本看不出意思表示解释的真正标准,更不用说规定意思表示解释的优先性了。况且,这种仅仅在《合同法》中的规定,远不如德、日等民法典在其总则的规定那样具有统领性和普遍适用性。
参考文献:
〔1〕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1-72.
〔2〕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9.
〔3〕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35.
〔4〕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M〕.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
〔5〕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谢怀颍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50-451.
〔6〕Brox, Walk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36.Aufl)〔M〕.München:Franz Vahlen Verlag,2012:44-47.
〔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Aufl)〔M〕.Heidelberg:C.F.Müller Verlag,2010:308.
〔8〕Zweigert, Ktz.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2Aufl)〔M〕.Tübingen:J. C. B.Mohr Verlag,1984:1.
〔9〕Enneccerus, Nipperdey.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5.Aufl)〔M〕.Tübingen:J.C.B.Mohr Verlag,1960:1030-1035.
〔10〕Flume.Das Rechtsgeschft(4.Aufl)〔M〕.Berlin:Springer Verlag,1992:450.
〔11〕Larenz, Wolf.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Aufl)〔M〕.München:C. H. Beck Verlag,2004:671-672.
〔12〕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7.
〔13〕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d.Ⅰ)〔M〕.Berlin:Deil und Camp Verlag,1840:206.
篇(7)
【关键词】工商变更登记 准法律行为 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
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类型)是行政法学上进行理论思考、体系构建的有效工具。正如拉伦茨所言:“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充思考形式是类型。”[1]那么,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类型)对于行政审判有何意义呢?司法实务者为什么也揪住工商登记行为的性质不放呢?
一、行政行为性质—不可回避的案件审理前提问题
(一)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行政案件案由。行政案件案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的概括。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月14日的法发[2004]2号《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规定,确定作为此类行政案件案由的基本方法是划分案件的类别,以行政管理范围为“类”,以具体行政行为种类或性质为“别”进行构造。案由的结构应具备行政管理范围和具体行政行为种类两个要素。据此,行政行为性质(种类)的界定就成为确定行政案件案由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点,对于行政案件案由的准确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行政案件案由的准确确定,能够帮助法官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定性”,有助于法律事实的客观化、类型化,也有利于把握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便于组织诉讼活动。
(二)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时首先要审查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自然人和法人成功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之一,而要对此作出合法、准确的判断,必须正确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除了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其基本界限外,还以明确列举的方式对应当受理和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行为作出了规定。而且,无论是对受案范围的肯定列举还是否定排除主要都是以行政行为的种类为基础的,即列举的是不同性质和种类的行为。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的行政指导等。由此,行政行为性质(种类)的准确界定就成为判断和认定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要前提。
(三)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法律的选择与适用。众所周知,我国的行政立法除了依据行政管理的具体事项制定相应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如《消防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之外,还制定了基本性、综合性的法律,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及正在起草的《行政强制法》等。因此,行政机关就某一具体事项作出行政行为时,除了依据专门性法律、法规外,还应遵循和符合前述的基本性、综合性法律的规定和要求,特别是在具体性的法律、法规对有关内容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更要依据基本性法律的规定作出行政行为。这也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审查和裁断的基本问题。而人民法院欲对此问题作出准确的认定,首先必须准确确定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因为,只有在确定行政行为的性质之后才能确定应当依据和适用哪一个基本性法律,否则,人民法院的裁判在法律适用上定会出现错误。
综上,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已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行政案件审理的一系列过程(诸如司法审查的标准、强度及裁判方式的选择等),成为人民法院正确裁判行政案件必须先行解答的问题。
二、工商变更登记不属于准法律行为性质的行政行为
关于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性质,司法实务者新近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工商变更登记有别于行政许可,亦非行政确认,而属于准法律行为性质的行政行为。[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商变更登记属于行政许可,并认为已得到行政许可法的确认。[3]对这两种观点,我们均不敢苟同。关于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准法律行为性质的行政行为的论述理论性较强,涉及行政行为的诸多理论问题,需要全面、细致地解析才能充分、有效地予以驳斥。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是一个已被抛弃和淘汰的分类结果。“准法律行为”是德国早期行政法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指公证、通知、受理等一类行为。然而,在当今的德国行政法学上,一般只有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之分,单独的准法律行为概念已不再存在。[4]在法国行政法上,公证、通知、受理行为归属于事实行为的范畴,也不存在准法律行为的概念。[5]在日本,将行政行为区分为法律行为之行政行为和准法律行为之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持狭义说的学者的观点,此种分类根源于德国学者柯俄曼倡导形成的传统学说,这种狭义说曾经是日本行政行为的通说。但如今,由东京大学田中二郎教授倡导,得到京都大学杉树章二郎教授和杉树敏正教授等积极响应的关于行政行为界定的最狭义说已成为日本之通说,也与德国的行政立法对行政行为的定义基本一致。[6]如芝池义一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的行使,对外部赋予具体规范的法律行为。”[7]而且,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持最狭义说观点。[8]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行为概念也有最广义说、广义说、狭义说和最狭义说四种,狭义说是现今台湾地区行政行为的通说。[9]狭义说对行政行为的界定是:行政行为系指行政机关就其职权行使所作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行为。[10]管欧先生也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以发生公法效果的行为。[11]
综上,将行政行为区分为法律行为之行政行为和准法律行为之行政行为只是日本、台湾地区传统行政法学的见解,现在都已被新的学说所抛弃和取代。质言之,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主流学说和观点早已不再秉持准法律行政行为的概念,即不存在所谓的没有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试图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落后的和早已被淘汰的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我国大陆当下行政法实践中的问题显然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
其次,前述观点的理由之一是:“这种登记行为不包含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只代表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12]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其一,“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必然存在一个旨在通过行政权的行使追求法律规定的制度功能实现,即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意志,该意志即构成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13]其二,即使是日本传统理论中的准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概念,其中也有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只是这种意思表示是效果意思以外的行政机关的意思、认识、判断的表示。[14]有关论者在引用上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时并没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说,工商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实与判断的过程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及其主观意志的表达过程,即运用法律这一客观标准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种类、数量、形式及其它方面的要求作出认定的过程;工商行政机关对申请变更的事项在审核后予以记载、登记在专门的登记簿上的行为,即作出变更登记的行为本身就是工商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与公安机关通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作出罚款处罚、规划部门通过颁发规划许可证对建设单位的工程建设申请作出许可的意思表示并无任何本质的差别,其区别也许只在于没有一个易于辨识的载体而已。那种所谓的“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登记机关履行的是核实与记载的职责,并未作出意思表示”的论断是人为地割裂了核实、记载与意思表示的一致过程。
再次,前述观点的理由之二是:“这种登记行为的效果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15]这一理由更是不能成立。其一,所谓的行政行为的效果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依据行政法原理,任何行政行为都是法律的一种实施,是法律目的和内容在相应领域或事项上的表达和表现,即行政行为是具体化的法律,是将法律的目的和效力作用于具体的事项和对象的桥梁和工具。因此,行政机关无论作出何种行政行为,都只是在表达法律的要求和目的,行政行为的效果当然也只能源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基于行政机关自己的意思表示。其二,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律效果是对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的确认和宣示,表现为证权性功能,目的是建立信赖关系和保障交易安全。这种法律效果正是工商行政机关作出变更登记行为所追求的,而不是前述观点持有者所说的与工商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没有关系。因为,“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是行政主体根据法律规范所作的意思表示所追求的,……。”[16]如此,作为行政行为具体类型之一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当然具有上述特点。
事实上,某种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所追求还是由法律直接规定,仅是学理上区分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的标准。[17]“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只代表登记机关对特定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并没有为行政相对人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18]以此作为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属于准法律行为的理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为行为对象设定、变更或免除任何权利义务,而仅仅依据法律的规定产生法定的法律效果,如答复、受理、通知行为等。这类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法上的行政事实行为。”[19]而行政事实行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被归入非行政行为的范畴,即不属于行政行为。[20]
最后,如果把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定性为准法律行为,那么在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框架下根本无法进行审理。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构造前提和规范对象的,而未将所谓的准法律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21]既然这样,作者如此煞费苦心地将变更登记行为界定为准行政行为又有何实际意义呢?对解决实际问题又有什么助益呢?也许有人说立法终将修正和完善,问题是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人民法院,在法律修订之前怎能明显违背法律的规定去进行裁判呢?这与我国法院的职责、地位和功能都是相背离的。
三、工商变更登记不属于行政许可行为
《行政许可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第12条第五项进一步规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据此,只有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才属于《行政许可法》所规范的行政许可。具体地说,工商设立登记、注销登记的目的正是创设或消灭法律人格,赋予或剥夺企业和其他组织独立主体资格,即确立或消灭企业和组织的市场主体资格或从事社会活动的资格,因而工商行政机关作出的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反之,如果某项登记不是确立或消灭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市场主体资格或从事社会活动的资格,而只是对有关事项的确认和记载,则该项登记不属于行政许可。工商变更登记只是对已经具有市场主体资格或从事社会活动资格的申请人的变更事项(如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权转让等)予以确认和记载,而非确立主体资格。由此,工商变更登记不属于行政许可。这一结论可以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04年1月2日作出的《行政许可法疑难问题解答(一)》中得到印证。该解答指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为,不包括对民事权利、民事关系的确认。因此,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组织机构代码、商品条码的注册,产权登记,机动车登记,婚姻登记,户籍登记,抵押登记等,不是行政许可。”
四、工商变更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有论者认为,尽管工商变更登记可以产生确认权利和事实的法律效果,但与行政确认具有技术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差别,因此工商变更登记不属于行政确认。[22]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把握工商变更登记与行政确认的关系时犯了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错误。理由是: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等型式化行政行为是依据各自不同的行为目的、法律效果和功能等进行划分和区别的,即行为目的、法律效果和功能是把握它们之间差异的根本,其它诸如程序构造、技术水平、裁量空间、审查方式等形式上的差异都只是细枝末节的部分,不足以成为划分行政行为模式的标准。因此,在判断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具体种类、类型时,应当主要从行为目的、法律效果和功能等方面人手。
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23]工商变更登记在行为目的、法律效果和功能等方面与行政确认一致:在行为目的上,行政确认是对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甄别、认定,以确定相对人是否享有某种权利及承担何种义务。工商变更登记正是通过对申请人已经变更的事实(如法定代表人的更换)或法律关系(如股权转让)的记载来确定和证明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在法律效果上,行政确认使得相对人获得了某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真实性、合法性的有效证明,而通过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人已做出的登记事项的变更就得到了行政上的确认,获得了最终的、完整的法律效力;在功能上,行政确认的结果仅仅在于确认或证明某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存在,并不产生权利授予的法律后果。无论是法律事实还是法律关系的确认,都有一种官方证明和公信的作用。工商变更登记的功能也在于证明登记在特定登记簿册上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经过了官方的审查和确认,因而使公众有理由确信它是真实的。综上,工商变更登记是工商行政机关通过对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己发生变更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加以审查、记载和确认,从而完成向社会公众进行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行政确认的内容和目的既可以是对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的记载和认可,也可以是对存在争议或模糊不清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的甄别和明确。由此,那种认为行政确认必须以有争议的或不确定的法律问题存在为前提,只是对处于模糊状态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进行甄别判断并加以确定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五、余论
如前所述,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法律的选择与适用。这里的法律适用主体不仅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作出裁判时,如果没有准确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就会在法律适用方面出现错误。譬如,在钟满薇不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准予股东变更登记一案中,[24]法院认为被告没有依照《行政许可法》第34条、第36条的规定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等实质内容进行全面审查,也未就该申请内容是否直接关系到股东重大利益的巨额股份无偿转让这一重大事项予以核实,因此被告作出核准变更登记适用法律错误。最后,法院依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第1款、第3款及第36条等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决定。我们认为,该份行政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因为,如前文所述,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而不是行政许可行为,因此工商登记机关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作出变更登记决定时就无法也无需适用和遵循《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既然如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时,当然不能以《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来要求被告,也不能依《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来评判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前述行政判决直接依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第36条的规定来确定被告工商登记机关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应履行审核职责并判决撤销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这个现实案例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准确判定行政行为性质对于行政审判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注释: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7页。Karl Larenz. Methodology of law[M]. Chen A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337 (2003).
[2]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公司变更登记司法审查的难点及其解决",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第39页。See The research team of Nanji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Difficulties of Judicial Review of Company AlterationRegistration and Their Resolutions[J].12 Journal of Law Application, 39 (2008).
[3]参见郭海云、袁玮:《论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行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15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章剑生:"行政许可审查标准:形式抑或实质",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99页。See Guo Haiyun, Yuan Wei. On the Review of Validity of Administrative Ca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Registration of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C].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vol. 15).Beijing: Law Press, 55(2005).ZhangJiansheng. The Review Standard of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 formal or Substantive [J]. 1 Stuies in Law and Business. 99(2009).
[4]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版,第6-7页;[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See Weng Yuesheng. Administrative Law and Morden countries of Rule of law[C].The editor committee of the series ofTaiwang university,6-7(1990). Hartmut Maurer.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M]. Translated by Gao Jiawei. Beijing: LawPress,391 (2000).
[5]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See Wang Mingyang.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M].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136(1988).
[6]参见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页。See Ma Shengan. On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M]. 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70-71 (2008).
[7][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See Muroitsutomu. Morden Administrative Law in Japan [M].Translated by Wu Wei.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cience and Law Press,81(1995).
[8]参见日本最高法院昭和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民集》第9卷第2号,第217页。最高法院昭和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及昭和三十八年六月四日的判例均有同类的解释。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See Jiang Mingan. The Course of Foreign Administrative Law[M]. Beijing: Law Press, 344(1993).
[9]参见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6页。See Ma Shengan. On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M].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ress, 74-76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