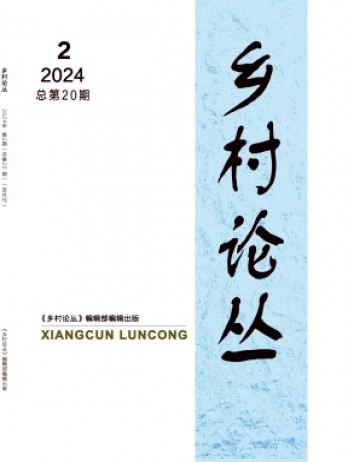乡村治理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08 15:29:44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乡村治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4]宋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篇(2)
关键词:乡村精英;村庄治理;东姜村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138-005
关于乡村精英和村庄治理问题的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梁漱溟和晏阳初等先生所做的工作。他们的探索,特别是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一种研究,更是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切关注大众生存环境的历史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自身微薄之力改变贫困民众生存状况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乡村精英与村庄治理,开始作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及村民自治的分析框架。村庄治理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本文是在2006―2012年对安徽省东至县胜利镇东姜村持续调查、观察的基础上,对东姜村“五老会”的缘起、作用及未来走向进行的研究,试图为乡村精英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案例。
一、乡村精英与东姜村“五老会”
1.乡村精英在乡村变革中的作用。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被学者称为中国乡土社会带有“神奇”色彩的变迁[1]。这种变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社会生活的自主参与,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强力渗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及其权力组织的规范性重构和制度性安排。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催生上层建筑的裂变;另一方面,来自自上而下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运作实践,村民自治作为官方力主推进的政治制度,在农村得到迅速地展开。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首先是整合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政策性探索[2]。在与基层村民的实际交流中发现,村民自治的运行离不开乡村精英的积极参与。
乡村精英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乡村精英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处于国家与村民互动之结点上,有着很强的内聚力和对村庄政治的控制力。[3]1978年开始的农村社会改革致使传统的、单一形式的政治精英形态的构成基础瓦解,然而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却导致了一些新的群体开始形成,他们或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或是凭借个人的人格力量、或是借助于农村社会中正在复活的各种传统力量来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从而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4]他们在社会转轨时期对农村社区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包括推动农村公益事业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整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等等。乡村精英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如何,政治参与的能力怎样,极大地影响普通村民。同时,乡村精英的态度和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的政治面貌,并将主导村民自治的运行过程和实效。发挥乡村精英的正向带动作用正是由形式化民主转为实体性民主的关键一步。[5]
2.东姜村基本情况。东姜村地处华东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安徽省东至县的升金湖畔,由原姜坝和卫东两村合并而成,全村4612人,在外务工有1489人。东姜村村民以周姓为主,村上有据说建于明代的周姓祠堂,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大规模翻修过。村民介绍说,过去每年这里的祭祀活动都很隆重,但解放后,祠堂日趋衰败,破旧倾斜,杂草丛生,上世纪80年代曾经成为多家村民的猪栏。这个祠堂在2005年由“五老会”发起村民捐资改建,现在里面除供奉据说是周姓最早迁移本地的祖先,还供奉宋姓、李姓、王姓等姓氏的祖辈,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恐怕很难发现一个姓氏的宗祠还能供奉其他姓氏的祖先!大量的研究和实证都说明,中国村庄的纠纷往往缘起于宗族矛盾,但在东姜村却没有,各个姓氏都和平相处,据说从大姓周姓祖先来这里定居以来,这里就没有发生过宗族之间的冲突。
3.“五老会”基本情况。“五老会”是由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族长、老教师、老村民组长等乡村精英自发组成的自治组织。东姜村的“五老会”成立于1995年,到2011年“五老”共有11人,平均年龄72岁。“五老会”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与文化、教育有关。“五老”成员基本上是按照城里人的上下班作息制度,村文化室是他们的办公场所。村里发生的大事小事,“五老”们也一清二楚。老支书说自从成立“五老会”,他有事做了,感觉比做支书时还有劲。另一老干部说,过去我们做事经常没有谱,现在不做干部了,我们还可以看着村委那几个人别做坏事。“五老”中以老教师最有号召力,所做的工作也最多。“五老”们不仅见多识广有威望,具有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而且有的还有较高的退休金收入,还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由于“五老”的无私、热心,而赢得村民尊敬;“五老”因为公正、办事实在,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而成为村庄治理和影响村庄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
二、“五老会”在村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1.组织文化和教育活动
组织文化体育活动。1996年,“五老”们不忍心看到原先的村民文化活动室濒临消失,牵头并发动村民们捐资3万多元,对房屋进行了清空和加固维修,但其功能一直未能发挥。2006年春节前后,见到村民们无正常、健康的活动场所,闲暇无去处时,只能靠打牌赌博、看电视打发空闲,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淳朴、团结、积极、健康、文体活动多的乡风村俗正受到威胁,“五老”们聚在一起,并召集村民代表座谈,商谈复兴村文化活动室。他们首先成立文化室自治管理组织,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再次发动村民捐资。村民们自觉踊跃捐了4万多元款,为文化室添置了桌椅、电器、健身器材,“五老”又发动村民捐书,还到镇上、县城等地方,通过各种努力,寻求各方支持,建立起东至全县活动场所最大、活动内容最多、管理最为规范的村级文化室。文化室内设阅览室、陈列室、文艺室、台球室,屋外的水泥场地上设有灯光戏台、乒乓球桌、羽毛球场、篮球场、老年垂钓乐园。
组织为留守儿童辅导学习和培训。由于父母双双在外务工,东姜村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200多名。一到假期,这些无人照看的孩子就成了在外务工家长们最大的心病。该村的黄梅戏演出流传较久,群众基础较好,村里的文化活动室建起来后,“五老”中的几位老教师、老艺人就将这些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免费教授他们戏曲、乐曲演奏、腰鼓打击。村民们都对这几位老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一帮“野”孩子管住非常赞叹,更庆幸这些留守的孩子不但安全有了保障,还能学有所得。从2006年暑期开始,在家长们的配合下,“五老会”决定办暑期文化课集中学习班,由4名返乡度假的大学生义务授课。2010年暑假开设了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3个班,有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共有60多名学生入班学习。2011年,姜坝中学有100名学生参加中考,有30多名学生考取了省重点高中。
2.对典型事件的处理
对典型事件的处理反映了“五老会”在村庄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水利问题或由此引发的矛盾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时有发生。东姜村是由原姜坝、卫东两村合并而成的,原姜坝村属丘陵地区,有耕地1670亩,其中旱地780亩。由于旱地多,在干旱的夏季,用水浇地花费很大。该村有民主、罗坝两个抗旱站。民主抗旱站始建于1967年,渠道长1000米,有效灌溉旱地面积300余亩,负担民主等8个村民组。1982年前,抗旱工作主要是由村组织统一抗旱,统一用水,统一管理;l982年实行以后,村组统的功能逐渐削弱,抗旱主要由村民自己解决。1989年,民主抗旱站的机泵设备被盗,1995年,站房倒塌。村委会认为该站已名存实亡,沟渠亦无修复可能,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对粮站东边的部分废弃渠道进行了规划,建房6幢。这为民主村民组的夏季旱地用水问题带来了隐患,村民多次上访。这时,“五老会”的作用开始显现。“五老会”中的老族长,利用长辈和族长身份,与其中的怨恨最大的村民沟通;老书记出面帮其中的困难村民联系做生意的门路;而老村长出面做在外经商致富的村民工作,捐助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使受损村民怨气得以化解。并且,“五老”们一直奔波于县乡两级,联系改变种植模式,为留守的村民栽培耐旱经济果树提供技术和市场支持,寻找东姜村产业发展的长久之策。现在东姜村的水利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3.影响村庄治理
“五老”们的影响力决定了“五老会”在村治中的作用,而且以我们的观察,其对村庄各个方面的影响还处在自我强化之中。一方面“五老”们的超脱和无私,越来越受村民尊重;另一方面,由于“五老”作为村庄的长辈或族长等身份被默认,其在具体事件处理中正面效应进一步显现,其威严和威信得到继续强化。因此,他们对村委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一事一议”从提议、动员到召集实际上都由“五老会”来执行了,村两委往往变成旁听者。有村民向笔者反映,现在的村两委很怕“五老”们,这也许是村民对“监督”的一种朴实和善良的理解。
塑造村庄价值。村文化室实际上成为东姜村的公共空间,村民们特别是老年村民在这里因为沟通娱乐而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暑期回乡的大学生重新找回他孩提时期的乐趣,同时也体验了在城里没有的乡村美学价值;在外打工的村民很吃惊地发现他们的父母居然已经离不开村文化室了。他们原来一直担心年老父母无人照应,接到城里,自己还立足未稳。从这个意义上,“五老会”的工作是在塑造村庄的价值,形成对村庄的一种正面的评价机制,重塑村庄价值和村庄认同。这种村庄价值的重新发现还为“五老会”带来新的血液,吸引更多村庄在外工作的退休干部、教师返回乡村。
影响村庄舆论。“五老会”对村庄舆论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村民认知的影响,即对村民的示范、价值导向作用,形成共同出力为村庄做事的共同价值取向,增强了村庄的共同体意识。比如,翻建文化室的资金,首先是“五老”们拿,这一正面示范的结果是村民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后来修路,据说有的村民家因为孩子多,上学负担重,拿不出多少钱,就主动提出自己包下多少土方,作为自己的责任。还有的村民只拿出两块钱,大家也不怪罪他。这种动员作用的穿透力非常强大――那些长年不归家的在外积累了一定资产的村民,主动回来捐款。另一方面,是对村两委的舆论监督。“五老会”成员内生于农村“草根社会”,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非常活跃,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乡村之外也有着比一般农民大得多的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有“敢站出来说话”的胆量和勇气,敢于出面“代表”农民利益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在村民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村民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矛盾的另一端主要是镇政府和村两委。“五老”中的一个老书记说,过去我们只知道满足上级的要求,经常害苦了村民,而且自己也不自觉地滋生了盘剥村民的恶习。现在退下来了,成为局外人,看事情更清楚了,更知道乡亲们需要什么,也就不怕得罪人了。另外,相比其他村民,“五老”们表达的利益诉求活动又是理性的。因此“五老会”在村庄治理上,发挥了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同时也成为对村庄干部约束和监督的主要力量。
三、进一步的讨论
1.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转换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乡村建设,应是农村全面综合改革的更深和更高层次的探索,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准或者说福利水平。乡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设的新乡村建设与之相通,即重塑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当前的农村正站在新一轮大变革的门槛上,取消农业税后,催生一种“倒逼”态势,把农村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当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与城市化和市场化有关。正是城市化和市场化,使得人财物流出农村,从而引起农村的严重衰败。东姜村的情况是,一方面全村4612人,在外务工的就有1489人;另一方面,根据老会计的说法,近十年间劳务和经商带回的存款有100万,除了部分村民建房取回部分存款外,村民做生意或购置农机具获得贷款的机会基本没有。所以东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村。可是在城里获得立足的机会非常困难,有好几个近年毕业的高中生也进城试图获得工作机会,但在碰壁后回到村庄,无所事事。一个老教师说,不到城里给政府添乱也好,但总得有事做才行。在祠堂四周,我们看到有前几年盖的楼房人去楼空,已经显露破败的景象。
中国有9亿农民,在城市吸纳巨量农村人口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也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已经成为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虽然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城市化吸纳农村人口,但在中国农村人口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几代人努力完成的任务。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在城市化和市场化以外,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但不仅是财政转移支付)介入乡村建设,以使农民所依托生存的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避免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将农村衰败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内,使农村成为助推中国现代化的力量。在漫长的转型过程中,乡村建设的一个目标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为他们提供福利,让农民也能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五老会”发起的文化建设,一头是让留在乡村的年龄较大的村民欣赏或参与,另一头是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们――因为大都父母不在家,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学吹拉弹唱,孩子们乐意参加。这里的民间文化活动,包括传统戏剧表演一直没有间断,继续作为乡村特别是传统节日的重大活动,对传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老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也说明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即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前提下,通过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通过发掘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智慧,通过提高生活质量,而非提高消费数量的办法,建立以人为本的新的生活方式。新乡村建设要让农民可以获得主体性体验,让农民从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做人的尊严。
2.吸引精英回归和培育新的“草根精英”
市场化、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优秀青年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从而导致农村优质资源的外流。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同时也就成为在城里难以立足的乡村打工者的心病,也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工钟摆一样的在农村和城市间摆动。通过美好农村建设,增强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让农业和农村成为吸纳人口的主要蓄水池,这就具有了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意义。但从东姜村的现实来看,年轻人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特别是对快餐式文化的接受,对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已经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老一代人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进入城市闯荡的年轻人又普遍生活不如意,即使是务工和经商有些积累的所谓成功者,也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乡村建设也不可能依靠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来建。“五老会”所做的乡村文化建设也需要注入新鲜元素,这样才能一方面使其有长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才能吸引年轻人。而这都需要年轻一代的加入。笔者与两位老教师交流过程中,有意引入这个话题,试图对“五老会”的未来发展与他们共同探讨。他们很焦虑,但更多的是无奈。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乡村精英的接替,就是要提高农村的吸引力,如何从两个方面培育乡村精英的接替力量,即让走出去的农村精英一定程度的回归,同时培育没有离开乡土的年轻村民对乡村的认同。因为让村民也感到与城里人一样,过上体面和尊严的生活,对未来有预期并充满信心,是精英回归和新的“草根精英”诞生的关键。让年轻一代对乡村生活满意,也就成为乡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3.建立乡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组织化的转换机制
对“五老会”自身的发展,“五老”虽然充满信心,因为陆续有新的“老”加入,队伍扩大是没有问题的。但“五老会”自身的建设和管理,他们还没有更多的关注。“五老”们做事基本停留在自觉的层面,内部没有考核、激励机制,也没有对未来走向的考虑。笔者的建议是,根据“五老”成员各自情况和特长,将“五老”的工作进行适当分工,并考虑适当的接替人选,保持“五老会”的长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五老会”这种建立在正面示范效应基础上,得到村民认可的监督,虽然作为村民自我管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发展到有可能代替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五老会”不能发展成为村民事务的执行机构。“五老会”存在的民意基础或者进一步的法理基础,也决定了其更适合作为村庄的议事和监督机构。目前迫切需要把已经成型的一些做法,比如文化建设、留守儿童的管护、教育培训等制度化。特别是,对村庄事务的监督,也要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正面的舆论压力,形成对村两委的提醒、说服和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引导乡村精英正面作用发挥的同时,要探索建立对乡村精英的培训和提升机制,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监督的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依法治理的乡村精英,形成持续推动乡村社会事业发展和民主进程的精英队伍。更进一步,要充分研究乡村精英治理的作用与局限,找寻乡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组织化转换的途径,在现有治理资源的基础上调整和重构乡村权力结构,让乡村精英的功能在民主治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是村民,要从体制上保障全体村民的政治参与朝着合法化、理性化、规范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平 “草根”民主走向制度化[J].中国改革, 1998, (12).
[2]张艳.乡村民主的塑造:制度创新与精英主导[J].晋阳学刊,2004, (5).
[3]林修果,谢秋运. “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篇(3)
2015年3月12日,本刊记者来到绵阳市三台县黎曙镇旗山村油麻灯梁子脚下,顺着路边一块“萧家祠”的红色指示牌,沿着羊肠小道走去,拐了好几个弯,来到一座庭院。
“水有源,树有根,人之于世,必先有祖。问祖归宗,宗则有家,家者祠也……”这是萧氏大宗祠里的一段话。
青砖灰瓦、石阶地板、画栋雕梁、红烛青香……祠堂的正中间,摆放着“萧氏历代高曾祖考/妣之位”的神龛,两侧是对联“西汉宗功垂万古,南朝世泽著千秋”。墙壁上布满了列祖列宗中“成功人士”的画像,其中最耀眼的当然是萧何了。另有几处碑文,详细地介绍了重建祠堂的来龙去脉。
三台萧氏是汉丞相萧何的后裔。这里也是近几年来四川恢复得较好的祠堂之一。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祠堂正在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而另一些人却“逆流而动”,兴致勃勃地干起了重建祠堂的事。
贤者谋篇与族人捐资
带领记者参观祠堂的是萧家的现任族长萧家顺,78岁,精神矍铄。老人早年间搬离旗山村,住在中江县黄鹿镇,这次回来,是商讨春分祭祖时“宗族理事会”的换届事宜;与其同行的是71岁的萧清富,是宗族理事会里的会计。
20多年前,萧氏在省内外族人的推动下,成立了宗族理事会。设会长(族长)一名,副会长4-6名,常务理事若干名,会计和出纳各一名。“我们这个理事会,很规范,几名常务理事组成了监委会,专门监督账目。”萧家顺指着一块碑文上面的“组织架构图”介绍说。理事会3年一改选, 萧家顺和萧清富已经连任了两届。
2009年,以萧家顺为会长的新一届理事会,在全省46名萧氏后人的发动下,倡议全族重修立足全川的萧氏大宗祠,举族相赞。原则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项工程前年竣工。据“萧氏大宗祠功德碑记”上的记录,参与出资的共有856户,总金额近65万元;另有“以劳折现视为捐币”的134人,折资约13万元。所有出过资的人,名字都被记载在功德碑上。
按照这种“贤者布局谋篇、族人捐资投劳”办法的,不独萧氏一家。本刊记者探访的另一个祠堂――成都市龙潭镇威灵村的范家祠,重建时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当时,首倡重建祠堂的是范氏“族长”、范仲淹第29代后人、龙泉驿范仲淹文化联谊会法人代表范文珏。“当时算了一下,要花40多万,上哪找这笔钱?”最终族人们纷纷捐钱捐物,范家祠的墙壁上现在还贴着几张红纸,上面记载着每户的捐款金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认为,为建祠堂筹集资金,其意义并不止于凑钱造一个建筑物,它背后的民间动员和乡村公共精神,是更值得关注的。
公共精神与族人自治
一般来说,为建宗祠出资最多的,总是那些“在外面干大事”、“不差钱”的族里人。但实际上,萧氏建祠时出资最多的萧清富,从部队退伍后一直是农民,现在每个月也只有400元抚恤金;而出资仅次于他的萧家顺,退休前是黄鹿镇畜牧站站长,收入也很普通。
这两个收入并不高的人,为何对这件没有回报的事情热情如此之高?萧清富说:“这是家族内部的公益事业,我们的年龄比较大,要给年轻人带个好头。”
重建祠堂的多是大家族,而祠堂本身是家族变迁史的集中地,祠堂祭祖还是众多的家族成员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通过祠堂祭祀,可以让后人更多地了解到族谱、族规、族训的文化渊源,加强血缘关系,联系族属感情。
虽然重修祠堂只是一个家族的内部事务,但账务管理却特别规范。在萧清富家里,专门有两个纸箱存放着“捐收账目清单”、“宗祠修建用工记录”、“固定资产登记”等各种账本。任何家族成员若对账务有疑问,都可以到会计这里查账。“捐多捐少,哪怕是只有50、20,也是‘勿以善小而不为’”。
有学者认为,重修祠堂是宗族精英的号召力及家族成员的互助精神所形成的,而族人自治,某种意义上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之一。
在古代,祠堂在很多时候充当着族人的“衙门”,几乎所有的族内纠纷都在祠堂里解决。今天虽然已是法治社会,家规不得与国法相悖,但族人们依然希望有一部分德高望重、处事公平的长者,能继续发挥调解族人矛盾的作用。有的村委、居委解决不了的问题,经他们出面后却可以很好地得到化解。
而在祠堂文化更发达的广东和福建等地,“族人自治”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的陈氏,于2012年筹资修复宗祠,总投入达800多万元,其中海内外陈氏后人捐资达600多万元。目前,陈氏大宗祠已形成三级议事机制:日常小事由常委会解决;涉及到动用资金较大的项目,则必须由19人筹委会讨论通过;而事关宗族大事的议题则要让村民代表、村中父老参与。其民主议事等自治事务管理模式已见雏形。这正是宗族力量和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
宗族“涉政”边界与影响
据华中科技大学乡村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的研究,在华南及江西等宗族力量发达的地区,常常整个村都是一个姓,村庄结构与宗族规范匹配完善。从村庄治理的层面来看,因为整个村庄都存在“自己人”的认同,村庄公益就与村民的私利之间有了较多重合的边界,这种村庄中的公益事业就较容易做成。并且,在宗族组织可以起作用的村庄,村干部不大可能与县乡结成利益共同体,“因为村干部最终还要在村庄生活,还要有脸有面”,宗族可以成为一股制约村干部权力的力量。
而在川渝地区,据贺雪峰的研究,虽然也有宗族,但影响力远不如华南地区和江西的宗族。
比如旗山村,萧姓占60%左右,其他大部分村民姓赵。目前,村支书是赵善勇,主任是萧仁福;而在上一届,则是支书姓萧,主任姓赵。多年来,村两委都是萧、赵两姓的人搭配,似乎是在维护着两个大族之间力量的均衡。但据萧家顺说,村两委并不干预两个家族的内部事务,而宗族也不会干预村务,这里面有着一种微妙的默契。
篇(4)
关键词: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2-03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领域,学者邓大才认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种: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纷繁,但并没有重视农民个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从农民视角出发,沿着“文化――心理”这个研究路线,将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最早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坎贝尔,他认为,“所谓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亦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继坎贝尔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众对自我政治能力和对政治客体回应自身需求的主观感知。
将这一概念置于乡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会对治理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村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对村民的诉求有所回应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能力判断。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能够对村委会、政府官员、乡村政治事务及政府行为施加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村民对村委会、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对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重视并有所回应的主观感知。
2.乡村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乡村治理定义为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广大村民、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管理的过程,最终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这一概念是对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多元性、过程的自主化均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谈判、协商与合作管理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的关键词。
(二)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广泛的主体――村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维度感呈现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以及政治事务的认知和情感,因此运用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一面向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作为村民参与基础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首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乡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基础,同时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会在正常的参与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这一改变过程与强化理论非常相似。根据强化理论的作用机制,如果村民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参与到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够影响决策结果,那他们便增强了自身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信心,这种正强化过程使得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得不到重视,那他们的挫败感就会增强。所以,通过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国这么多年乡村治理的状态。
2.乡村治理权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体系必须对村民的诉求予以回应,这将导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终至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达到均衡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了权力的多元化配置。乡村治理理论的权力配置多元化承认了乡村社会的私权力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国家权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呈现出上下互动的双向运行过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影响村委会和政府的决策进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视与回应,村委会和政府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在互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现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
3.乡村治理过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将导致村民更为熟悉村级地方政治环境,因而村民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乡村治理的正常体现。
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不同政治层级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相对于接触较少或比较陌生的国家层次环境,在地方层次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我国村民政治环境背景,分为“村级”政治层级和“政府级”政治层级(村级以上的政治环境层次均认为是“政府级”)。同时,在更为熟悉的村级地方环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应表现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乡村治理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山西省北、中、南部选择了7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这7个村庄有些是传统型农村,有些是现代化新农村,有些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后,通过随机选择,在保证男女比例相当、家庭收入与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匀的前提下,进入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和访谈,最后共获得802份有效问卷。基于已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总体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体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4589(<2.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据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理论,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为合适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国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为剖析乡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95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108(>2.5),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内低外高”特征。
这说明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了解不多,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影响力不足,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政府、村委会极高的信任和极强的依赖,期望他们重视并回应自身的需求。
从表3中可以发现,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村民“影响型”政治效能感(2.3974)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知识储备库,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动力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规章制度、选举程序、村委会运作方式不甚了解,对乡村公共事务不甚关注。
“影响型”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效能感,体现行为意向的特征,会直接导致村民政治行为的发生。而表中数据表明村民对影响政府、村委会干部的主观感知也不甚强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从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村民“重视型”(2.5787)明显高于“回应型”(2.3918)。
这说明村民认为政府及村委会比较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对于有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访谈中就会发现,很多村民认为政府出台各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当具体到政府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很多村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质疑。
(三)村民政府级、村级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村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591,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406,政府级的明显高于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
这说明村民对于政府级的环境层次的主观感知更为强烈一些,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这说明以“乡政”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已经深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不利于农村农民社会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表6中,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进行比较,仍然是政府级高于村级。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征,与我国目前“行政化”和“空壳化”的村委会密不可分。这些在社会流动很弱的乡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内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对政府级更为熟悉,更易感知,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所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出发,审视乡村治理在主体、内容、性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
我国乡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广大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其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们认为无力作用于治理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不会得到重视与回应,那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只是个与自己无关的、形同虚设的制度。其次,“乡政村治”模式中,“乡政”与“村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权力运行方向不一致,在乡政村治的具体运行中,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博弈,以期达到协商合作,合力共赢的状态,最终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村治”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体偏低,认为参与“乡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对一大主体的缺失,那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远。
(二)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内容:内容失衡
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现“内低外高”的特征。较低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认知能力和影响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必将影响村民自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对政府以及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和依赖,这虽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村庄的自治性。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性质:偏离治理性质
乡村治理强调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强调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乡政村治”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与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级地方政治环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应该更高。在农村,无论是作为自然村的熟人社会还是行政村的半数人社会,村民对于村委会和村干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认为,相比于包括“乡政”在内的政府级的政治环境,村民对于“村治”更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村民在村级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级的。那么,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的乡村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有违治理的本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已获得的802份有效问卷的量化分析,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村民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内低外高”的特征表明乡村治理内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级上的表现,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浓厚,偏离治理性质。总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测试维度为我们展现出目前乡村治理的全貌,从中折射出我国30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学习与探索,2012(1)
[2] Paul R・Abramson .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4] 李蓉蓉.政治效能感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现实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12(4)
[5] 李蓉蓉.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0(9)
[6] 阿尔蒙德,维巴.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张志英.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路径的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
[8] 郭秋永.抽象概念的分析与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例释.见第二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文集,1991
[9]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3)
[11] Shuna Wang,Yao Yang.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07 (10)
[12] Zhang, X,Fan,S,Zhang,L& Huang.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12)
[13]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巴林・顿莫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
[15] 黄兴豪.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持续与变迁.台湾民主季刊,2006(2)
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化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5-0055-05
农民的政治参与,从有序性、规范性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个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相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而言,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甚至是通过违反法律规定的参与方式所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它属于无序政治参与的范畴。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利益多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农民广泛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愈发强烈。农民追求自身利益的主流,是通过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来满足,这也是每个农民都希望采取的方式和渠道。但问题是,一旦合法的渠道不能畅通,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必然选择。而当前,农民的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正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事态的发展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稳定。为防止陷入现代化的“中等收入陷阱”[2],使乡村治理在良性轨道上和谐运转,必须努力化解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一、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基本表现形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利益的追求不断增长,农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和行动呈现出迅猛增长之势。这对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不断扩大,其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越级上访
所谓越级上访,是指人员反映问题,不是到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反映,而是直接到更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反映,或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经受理并正在办理时,又到更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反映。[3]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时期,农民上访的主要根源性因素是征地补偿、环境污染和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等问题,尤其是因征地补偿问题引发的群体上访,持续性升温。我国现有的征地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补偿费用偏低,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用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更谈不上拿出一部分资金创业发展。在制度性参与和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失地农民慢慢演化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失地流民。仅2005年,全国共发生因土地引起的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就高达19700起,占农村的65%以上。[4]对农民的上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的部门或上级行政机关,要么将意见转交给有关部门,而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后期的督办和检查,要么对农民的呼声漠然视之,甚至斥之为刁民闹事,农民的利益表达往往石沉大海。在合理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
农民的越级上访,从本质上来说,是希望以更大的权力来纠正较小的权力,这是法制建设不健全时期的过渡性办法。但是,如果越级上访失控,尤其是规模大、涉及面宽、要求高、组织性强的群体性越级上访成为一种趋势,不但会严重影响正常的维权,增加上访农民的经济负担和政府的管理成本,而且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3]
(二)群体申诉
农民群体申诉型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农村。所谓农村,是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农民这一特定群体中的不特定多数人参与,经过一定的酝酿、组织和策划,围绕一定目的,而共同实施的、没有合法依据的聚众上访、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示威、绝食、聚众闹事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和行为。学者于建嵘指出,农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维权抗争型、突发骚乱型和组织犯罪型,其中维权抗争型事件占农村的90%以上。[4]
(三)直接对抗
在农村的快速转型时期,制度短缺是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政治需求普遍扩大和现行体制下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在直接的、有效的体制内利益表达严重不足甚至堵塞的情况下,在现有的一些制度安排流于形式的现实面前,在一些领导干部对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粗涉、不管不问的背景下,农民采用暴力的或激进的直接对抗,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来使政府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成为必然选择。[5]
所谓农民的直接对抗,是指农民基于对乡镇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不满,或认为自身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遭受到不法侵害时,拒不服从乡镇基层政府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管理,甚至暴力阻碍执法的行为。农民选择直接对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自身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寻求一种公正平等的社会心理。农民是社会资源拥有量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本身就很难有机会把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有效渠道反映到上级政府部门,体现在政策法规层面,但这并不表明农民不愿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参与活动,只是他们急切的参与热情被短缺的制度现实所阻断。这种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产生的强烈的内在参与冲动,一旦遇到利益侵害行为时,就会转化为过激的社会行为,以直接对抗的形式来寻求表达的需要。如农民因征地赔偿不公而拒绝拆迁、搬迁,甚至与拆迁人员发生激烈的直接对抗等。
二、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对乡村治理良性运转的挑战
当前大量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仅直接冲击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降低了乡村治理的绩效,而且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极大地破坏了参与型乡村治理文化的形成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政治文化建设是乡村治理中的一个深层次的内容。用治理的方法分析乡村政治,首先要分析的就是乡村的政治文化。只有农民在内心认可了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并在政治观上达到基本一致时,才会产生归宿于这个群体的高度自豪感,才会发自内心地去维护其价值观,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也会视其在可容忍的尺度范围内,社会整体是和谐有序的。
乡村治理的文化,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参与型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亨廷顿认为,所谓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6]。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先生对政治参与的界定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7]阿尔蒙德认为:“有利于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公民文化应该是既能够使过高的参与热情与政治冷漠之间达到平衡,又能使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与主动参与之间形成融合的一种政治文化。”[8]这种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制度化范围内,使农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与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达到一种和谐稳定的治理状态,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需求。
不可否认,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在多元化利益发展的现状下,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来保护自身利益是当前农民的主要选择,而一旦参与渠道不畅,公正难以得到保证,农民或选择非正式组织,或通过家族的势力,通过活动来达到心理的满足。权威的崇拜和家族势力的依附,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参与表象。而狂热的、非理性的直接聚众越级上访、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示威、绝食、聚众闹事甚至直接对抗,则严重破坏了农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严重干扰了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
马克思曾经指出,有时候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农民在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难以维护自身利益诉求时,必然会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心理需求。这种释放,一方面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促使相应的党政机关来关注民生的需求,化解现实的矛盾,推动体制的改革,满足农民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大量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却无形中干扰了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良性构建。
系统论认为:“在一个动态结构系统中,这种结构的功能是直接由要素之间的协调作用体现出来的。”[9]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治理,就是乡村社会各种社会资本、各个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其功能达到最大优化的状态。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农民对制度化政治参与不感兴趣,乡村社会的治理就会因缺少参与主体的支撑而走向失败。学者燕继荣指出,所谓社会资本,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10]大量社会资本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而且会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宏观治理网络。
但不可否认,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成本,延缓了政府集中力量承担社会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时间,另一方面阻碍了各种乡村民间组织的有序发展,破坏了乡村之间在改革进程中构建起来的信任关系,放弃了自身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在导致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能下降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态势。这也正是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1]。
(三)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直接降低乡村治理的绩效
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是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民如果不从国家或乡村建设的全局和我国建设中的实际出发,而是一味地为追求己利而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上访或者聚众闹事,既荒废了自己的农业生产,也不利于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村民发展经济,从而难以为乡村治理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干扰乡村民主进程。大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严重阻碍着民主进程的良性发展。非制度化参与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政治责任意识的丧失。民主不等于闹事,权利更不等于破坏力。乡村民主的核心,还是要通过有序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来维护农民的民利。三是增加政府治理成本。面对堵塞的交通、被强占的工地、聚众闹事的群体,面对越级上访、静坐请愿、围堵党政机关的农民,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的人员来疏导化解,增加了政府治理的成本。四是严重破坏乡村社会稳定。
三、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成功的关键
乡村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参与到乡村事务中来。面对快速转型时期农民的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给乡村稳定发展带来的极大隐患,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化制度外为制度内,化无序为有序,以实现农民对自身利益合理追求的最大满足。
(一)通过培育新型政治文化推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社会个体一旦认可政治价值观,就有归宿于这个群体的自豪感和为维护这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自身使命感,就会发自内心地去维护其价值观,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也会视在其可容忍的尺度范围内,社会整体是和谐有序的。[12]要真正实现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仅仅提供物质财富的支撑和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积极创建符合中国农民所需求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以推进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这是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为此,一要从积极参与、有效监督、恪守法规的角度努力培养农民的责任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利益;二要大力积聚社会资本,不断提高社会凝聚力,推动乡镇政府和农民的合作、信任和理解,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三要发展协商民主,完善表达机制,始终把公民的有序参与作为现代民主的精神,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和谐。[13]
(二)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硬性保障
当前造成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制度安排的缺失。要抑制和减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形成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环境,就必须突破制度的障碍,逐步完善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不断拓宽和逐步畅通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制度机制。为此,一要完善村民选举和决策的参与机制,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要始终坚持村委民选,让农民真正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并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增加候选人与村民的沟通、交流,让农民群众真正了解候选人的思想观点、参政能力和道德品质,农民才能选举出自己真正信任的、文化程度高、致富能力强、乐于为公众服务的人进入村民委员会。也只有经过农民真正参与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才能得到农民最大的政治认同。而且农民在参与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也不断创造出诸如吉林梨树县的海选模式、山西河曲的两票制、赣州的村民理事会等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新形式。二要拓宽参与渠道,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不断加强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进程,逐步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最大限度保证农村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都能选举自己代表的法律法规。要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积极推行多部门联合接访,在农村广泛建立固定的接访场所和信箱,配备专职人员,随时接待农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并不定期地组织党、人大、行政、司法等多部门人员积极深入农村,随时了解农村情况,及时化解农民的利益诉求,变群众的来信来访为政府部门的及时走访,以便把矛盾消除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可以及时有效改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13]特别是在当前由“民工潮”引发青壮年农民和乡村精英“规模化外流”,乡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大量“空心村”不断生成,农民自治主体虚置化的情况下,网络参与的作用就更加重大。当然,对网络参与有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也要提前预知,防止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网络化的生成。
(三)通过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管理环境
立足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宗旨,乡镇政府在职能定位上要从以前包揽一切的全能型政府向只提供核心公共产品服务转变,在管理模式上从以前的“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要通过引进人才、建设市场、提供信息、支持民间投资和搞好社会治安等措施,为本行政区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要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与村组的关系,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都要引导农民群众通过规范的方式和程序,民主决策,自主管理,而乡镇政府要更多地通过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在尊重村民自和村委会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对乡村事务的有效治理。[14]
减少农民非制度化参与事件,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让农民群众对事关自身利益的乡村事务真正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首先,乡镇政府要把年度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年度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等行政、经济管理活动,把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的发放和使用情况、宅基地的审批情况、计划生育情况等与村务相对应的事物,把乡镇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期限、监督办法等公开化、透明化。其次要公开村组事务。要把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村组财产和财务支出、集体土地和经营实体的承包、村干部的年度工作目标和工资奖金、征收土地和宅基地的审批、计划生育指标等农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村里的重大事项向村民公开,做到大事公开透明,小事清清楚楚。[14]
(四)通过推动乡村社会的自律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提供广泛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当前,我国乡镇村干部的腐败导致“信任”社会资本的不足,制度有效供给短缺对“规范”社会资本形成一定制约,民间组织的发育不良对乡村社会网络资本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滞。因此,在乡村社会资本发展方面,一要强化农民的自身素质,逐步提高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识、合作意识、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推动农民以更加有序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中,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二要强化有效制度安排,构建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度。制度如果能够给农民提供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与村民建立起有效的相互沟通的制度桥梁,就会极大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减少政治失序的可能性。三要加快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意味着农村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民通过民间组织,逐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提升农民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力量,推动形成乡镇政府与农民合作治理网络体系的形成,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6.
[2]蔡.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J].新华文摘,2008(6).
[3]龚志宏.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J].学术论坛,2009(8).
[4]于建嵘.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与防治[J].中国乡村发现,2007(1).
[5]孔桂丽.论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
[6]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
[7]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3.
[8]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5.
[9]黄顺基.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3.
[10]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8.
[1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89:38.
[12]刘勇.“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及心理疏导机制构建[J].云南社会科学,2010(1).
篇(6)
一、善治的思想内核
作为当今两大公共管理理论之一,提善治就得从治理理论说起。治理的基本概念,是指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体在面对人民共同事务进行不同组合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运用公共权威秩序,有序、协商、互动、不断进行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当面对各种冲突或不同利益时,各种行为个体在权力的引导下,本着互惠互利、原则,以满足自身的要求,同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是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持续不断互动的管理过程,是政府与个体互动合作的一种新颖的管理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平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稳定、廉洁、公正等元素。
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善治涵盖了民主、法治、参与、公正等价值性要素。而这些要素对完善乡村治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对乡村治理实施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调动了村民生产的积极性,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信赖和党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乡村治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乡政村治”体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存有两大弊端。第一,领导方式。地方政府的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的来源不同、目标不同。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乡镇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上级政府,而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各种政策性任务时需要村干部的配合,因此,乡镇政府就可能利用拥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利益诱导和激励,选出对其开展工作最“有利”的人选,达到村委会服从其“支配”的目的。第二,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欠缺。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威向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确保农村转型能够顺利进行,这对农村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保证了转型中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国家废除了农业税,使地方政府失去了财政来源。由于政府财源出现枯竭,造成了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已无力满足农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加之缺乏社会的应变能力,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缺乏有利民主政治环境。在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民主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要想参与选举并取得相应的利益却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由于选举是一种集体行为,作为集体行动的协调者,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越强,参选率自然越高,获胜几率越高。我国村庄是“半熟人社会”,当村民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无法达成共识、组成团队时,现存的村民组织便成了唯一选择。比如:以血缘关系和姓氏联系起来的宗族、教会及宗教组织,以地缘划分的自然村以及其他村民组织等;各种村民组织和利益团体通常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选举进行干预,但是并非所有组织都有强烈的动机参与选举事件。宗族是村庄中最为重要的动员者之一,但是其具有封建势力的狭隘性,不符合现代民主方向的要求,而教会、宗教组织的参与愿望则相对较弱。第二,乡镇政府利用相对于村庄所拥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积极干预村民选举。
(三)村民参与政治困难重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产生了参与政治的热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事务、实现民主决策的主要途径,但是在村务决策上,由于村委会和村民会议在事务划分、权限划分、决策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大
的模糊性,使得村民质疑程序的公正、透明性,也对产生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从而降低村民的参与热情。
三、以善治为目标,完善乡村治理
建立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最终达到乡村善治,既是政府的现实目标,又是最终目的。通过怎样路径才能达到目标?怎样才能做到以善治为目标,完善乡村治理呢?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政府应树立建设有限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的理念,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的惠民政策,改革行政管理的流程和内部制度,使能适应社会化、人性化、高效化的体制;规范政府权力,改变全能政府的传统形象,建立更加完善、运转更加协调的体系,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绩效等要求。而在地方政府方面,面对村民自治,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拥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工作;本着中立的观念对待村民选举,让村民感觉到地方政府是自己的知心人,依法监督村民自治能够有序、有效、公平、公正地运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丰富地方政府管理手段,从而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丰富公共产品品种,增加地方政府对村民的回应能力,以满足村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取得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二)培育社会团体组织,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不仅要优化政府内部组成,以利于其功能发挥,还要特别注意政府与社会的相动联系,建立市民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我国的政府强势、社会弱势地位的理念过去一度占统治地位,现在虽然强势政府比较盛行,但不是全能政府。要使我国全能政府状态有所改善,就得加强社会团体组织的培养和发展,建立和健全市民组织关系,培养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意识,建立政府与社会多角度、多层次的联体互动关系。社会组织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不受损害而自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社会组织和政府是社会的有机构成。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培育下,不断地健康成长、完善,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缺或的部分,社会组织监督和促使政府公平、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培育乡村治理力量:(1)要开拓政治参与渠道,调动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保证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真正实现村民自我治理。(2)要培育和发展健康的社会村民组织。(3)要充分利用健康的民间资本力量,建设一个政治面貌向上的新农村。
篇(7)
关键词 乡村治理 差序格局 理性化 礼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From the Battle of Etiquette to See New Rural Governance
ZHANG Siq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different sequence" (Fei Xiaotong, 1947) is now becoming rational. In the villages of China,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based on clan and kinship has broken, while the contemporary one based on law cannot be set up utter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village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al structural and government by law, depends on which, and attempts to advanc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differential pattern; rational; etiquette; law
1 新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理性化的差序格局
如今的中国乡村,只有特别小的村仍然是熟人社会,而在行政村一级,也就是目前大多数乡村,村民之间不是很熟悉,已然成为一种半熟人社会。在这种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被割断,村庄道德没有了结构上的支撑,村庄秩序因此变得愈加混乱(贺雪峰,2003)。
随着传统宗族、血缘、亲缘等传统关系的弱化,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发展。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贺雪峰,2003)。这种变化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
尽管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当前中国社会中种种行为的变化,却始终逃不出差序格局的藩篱,只是在此基础上修修改改。例如卜长莉在《“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特点都已经发生变化,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概念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卜长莉,2003)。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即当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的总体框架,但是局部已经发生改变,因此,“理性化的差序格局”能够更好地表述当前新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
2 礼法之争的原因分析
新型乡村中,礼治逐渐丧失其效能,而法治的建立又面临重重困难,若从根本上找原因,社会结构是首要的。以下笔者将分别从“差序格局”和“理性化”两个方面阐述礼法之争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在笔者看来,差序格局与法治秩序之间存在着以下三点具体矛盾,以至于社会结构成为阻碍法治下乡的根本原因。
第一,差序格局弱化了每个乡村社会成员的独立人格,而法治秩序正需要这种个体的独立性。乡土中国的每个成员都以“己”为中心,但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而我们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中,但是法治秩序需要人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保护自己法律权利,在受到威胁是真正做到“私”。
第二,差序格局中的人们对相同的事情会因为做事人的不同而有差别地对待该事件,而法律的权威性则是一种普遍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差序格局的“水波纹”中,公和私是相对的,个人站在任何一圈上,圈内的即为公,圈外的即为私。这种根据与个人的交情来判断是非的态度在法律条文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三,差序格局中人们的关系网络是可以伸缩的,即人们的判断标准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是法律是一种较为固定的社会规范,具有明确的规则和边界。人们关系网络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是非判断的模糊不清,而我们知道,法律条文的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斟酌的结果,不容许随意改动,具有完全的确定性。
3 折中寻求解决之道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当前中国的法律现状。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主要以制定法为法律构成,现在,许多的习俗是得不到国家法律认可和保障的,很多原则性的规范使得社会许多约定俗成的习俗丧失生存空间。对于复杂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来说,这样无疑是不利于纠纷的解决的。
其次,我们应该知道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法律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定纷止争。自制是民法最根本的精髓。总而言之,“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下转第91页)(上接第79页)就是好猫”,无论礼治法治,只要真正帮助农民定纷止争,就是最好的社会控制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增强法律的灵活性,建立多元化的解决机制。
最后,在当前这个礼治逐渐削弱,法治又无法建立起来的时候,笔者建议以一种折中的方法——庭外调解制度,来解决村民纠纷,进而加强乡村治理。庭外调解制度是一种便捷灵活的处理纠纷的方式,一旦成功,既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又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在相对较小的村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民们在纠纷解决之后还可以如往常一样相处。但是这种方法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他们的报酬理应政府支付,不然,农民的法律利益还没有得到保障,经济利益又再度受损。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