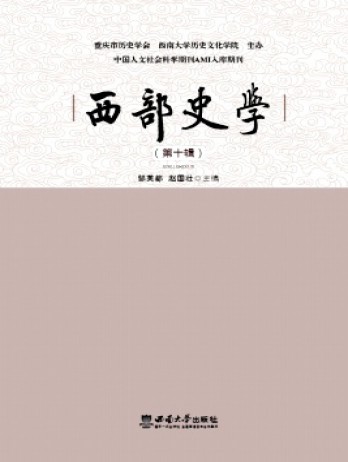史学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8-26 22:55:1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程千帆;文论十笺;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篇(2)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篇(3)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门类艺术;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与指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如何对待艺术学理论研究?
2011年6月中旬,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艺术学界引起关注,同时国内重要文艺报刊均作了专题报道和评论。其中,特别引起议论的焦点话题是,关于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定位,以及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在论坛闭幕式上有过发言,主要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方向的宏观角度来谈。现整理成文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艺术学界的同仁。
众所周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首要问题是涉及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此问题的确认,最为直接的触动莫过于是针对培养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以及培养方向的争论。这一话题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成立伊始,招收研究生工作以来就一直提起。我想,这也是我们与其他高校或研究院所共处于承担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所无法回避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换言之,作为一个学科,艺术学理论研究不能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没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产出。一句话,不能没有自身的教学常态和教学成果。否则,这个学科便难以持久维系,更无法前进。而艺术学理论学科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又最终都体现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上,即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所以,我所思考、所谈论的,可以说是从一个教学的具体环节,即从高校或研究院所研究生培养的终端,来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
现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是作为文学门类学科中一级学科,即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分类,目前艺术学界比较认可的是:1.艺术理论,2.艺术史,3.艺术批评,4.艺术管理。当然,还可以细分下去,但大致可以涵盖在这四个大类学科之中。这四个大类二级学科虽然都很重要,但从学科建设来看,它们之间还是应当有主次之分。比如说,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之分。像艺术理论、艺术史,就是比较典型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艺术批评与艺术管理就属于应用理论研究。这在其他学科序列中也同样存在,如经济学中就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话说回来,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总是该学科赖以成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是以艺术理论、艺术史这样的基础理论作为专业方向或者说是培养方向,这是很好理解的。而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抑或艺术管理,都离不开“艺术”二字,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二级学科、哪一个专业方向,艺术学理论都必须冠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都必须立足于艺术,以艺术为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就研究对象而言,艺术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艺术一般与门类之分;就研究路径而言,有从一般原理出发研究具体现象与从具体现象研究中抽绎出一般原理之分,用通俗的话说,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就研究角度而言,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就研究指向而言,又有举一反三与举三证一之分。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应该研究什么样的“艺术”问题呢?又应该以怎样的路径、角度和指向研究艺术学理论问题呢?说的具体些,就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有哪些论文的选题?又应当如何去做论文?这是我着重讨论的内容。
一、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
在谈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时,有必要先明确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一般说来,“艺术”是广义的称谓,即对各艺术门类给予的抽象总称。目前,我国关于艺术学的学科设置,就是以这个总称来命名的。而在各种艺术中,通常习惯将综合两种或是两种以上的艺术说成是综合艺术,这种方式占有很大的比例。借助综合艺术的概念来说,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其实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关于艺术的概念,通常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我想对这个概念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的艺术概念大多是广义的,不必说中古以前“艺”与“术”的所指①,就从晚清刘熙载的《艺概》与近代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②来看,我们的“艺术”概念也还是所有的艺术门类的总和。而西方人则把造型艺术视为狭义艺术,把包括音乐、戏剧和舞蹈之类的表演艺术,还有诗歌乃至文学视为广义艺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相对于作为门类艺术总和的广义艺术概念而言,既然造型艺术是狭义艺术,那么,表演艺术又何尝不是另一类“狭义艺术”呢?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诗歌、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狭义艺术”。所以,我们在谈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时,区分艺术的广义与狭义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它们指向的都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
这样解说“艺术”与“艺术门类”这两个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关于“艺术”的范畴概念,其实是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抽象。用哲学的术语来讲,“艺术”实际上是指“艺术一般”,是对不同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的指认。这里又有一个概念的细分,是说作为“艺术一般”的“艺术”,是有别于作为所有艺术门类总和的“广义艺术”。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认为“艺术一般”是从哲学高度对艺术门类的整体观照,而“广义艺术”则是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历史罗列。相对的说,艺术门类是“艺术特殊”,是艺术一般现实存在的具体形式。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与“艺术门类”(包括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设计、影视等)之间的关系,如同文学学(又有称“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学”与“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一样,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艺术学界的共识,即艺术学理论研究主要偏重思辨③,是对艺术活动一般规律的研究。所以,人们自然会认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最好是“艺术”(即艺术一般),至少是广义艺术(即对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考察)。这种看法并没有错,但不能绝对化、单一化,甚至唯一化。我们的研究生在做开题报告时,常常因为选择了美术、书法或音乐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质疑,说这不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更像是艺术门类的选题。这样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绝对化、单一化了,是对艺术与艺术门类之间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缺少认识的结果。哲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而特殊是一般的具体反映。没有特殊便没有一般,反之亦然。一般与特殊是相对而言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相对于文学,诗成了特殊;相对于风雅颂、离骚、汉乐府、建安古风、唐宋格律诗、近现代白话新诗,诗又成了一般。同样,在人文学科――艺术学――造型艺术学,再细化到绘画,乃至国画……,但凡在纵向范畴链中,每一个层级对上都是特殊,对下都是一般。因此,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以艺术或广义艺术作为对象,而是应该把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当作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对象。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是越抽象、越宽泛就越好,也不是一定要跨越多少艺术门类,这是因为,如果选取具有典型阐释意义的某一个艺术门类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同样可以讨论具有一般意义的艺术规律问题,那么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好选题。
如上所述,一般总是存在于特殊之中。诚如,艺术学之父、19世纪末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的研究是从绘画入手的,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艺术学学者、法国人保罗・梵乐希则侧重于诗学研究。举证费德勒、梵乐希的研究,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照抄西方人的那一套来建立中国艺术学;我们当然要结合中国艺术的特征、考虑中国具体的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我想说的是,借鉴西方艺术学研究,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美术学或者音乐学的研究论文选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个案研究,只要它能够指向一般,并对艺术门类有上升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的,甚至对其他艺术门类活动也有启示或参证的功能,它便具有了一般的意义,便可以视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形态,视之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因此,有一些艺术学理论研究选题与艺术门类研究选题相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是看其着眼点与结论是否指向一般。既然艺术学理论研究可以用艺术门类的素材为研究对象,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与艺术门类研究论文又区别何在呢?
我们认为,艺术门类研究与艺术学理论研究之间虽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但其中的区别是可以界定的。总体而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艺术一般,也可以是艺术特殊,但其研究指向必须是对一般规律的揭示。正像文学学(文艺学)领域可以有抽象的、跨门类文学的文学一般规律的研究论文,也可以有借助于文学门类研究而抽绎出文学一般规律的论文一样,艺术学理论论文无论是以艺术一般还是以艺术门类为对象,其最终都应当指向艺术一般规律的研究,否则,它便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及其应有的指导价值,便不能被视为艺术学理论论文。而艺术门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特殊,其研究指向可以是特殊,也可以是一般。一般规律可以包含特殊规律,但特殊规律的揭示却并不一定都上升到了一般,也就是说,艺术门类的研究论文中有许多命题并不需要上升到一般,或者研究者仅仅停留于具体论事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一般,这样的研究论文当然只能被列入艺术门类研究的范围之中。如果艺术门类的研究命题能够通过具体的艺术现象考察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即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既可以看做是艺术门类研究,也可以视为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的发展允许一定的交叉。
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
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
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
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三、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
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
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
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
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
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
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
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
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
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四、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以上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一般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从艺术学理论研究与美学(艺术哲学)研究的关系,谈论了我对艺术学理论研究论文选题的总体看法。接下来,我想谈一谈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与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密切相关的问题。
与其他学科一样,艺术学理论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广度;一是深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各自都可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
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
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
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五、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综上所述,在对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思考基础上,我想再来谈谈对本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这是本文探讨问题的具体落实,也是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根本所在。
首先,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既可以选择艺术一般为对象,也可以从艺术门类中找选题,关键是看如何去研究;只要研究生所作的研究不是陷入艺术门类无法上升,而是从艺术问题、艺术史料、艺术现象中揭示出隐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用以指导艺术活动、促进艺术发展,无论所选择的研究命题和对象在哪一层级上的,都应视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范畴,我们教师都应予以鼓励。
其次,在现阶段,应当肯定硕士生和博士生沿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也正因为如此,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在总结以往研究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每一位硕士生、博士生应该努力熟知两个以上的艺术门类研究,同时努力至少具有一种艺术门类的实践经验。如果该研究生缺少这些必备的研究条件,必须补修相应的课程。只有精通某种艺术门类,以此为根基,才能通过相邻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逐步做到触类旁通,跳出门类的的局限,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通”。当然,这绝不是仅仅读“艺术概论”所能获得的浮于表面的“打通”,而是深入研究之后的真正的打通。
鉴于艺术与艺术门类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要求基础好、已具备两门以上艺术知识的研究生做跨艺术门类的艺术学学位论文,但必须防止沦为大而空。同时,对于愿意立足于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之中,自下而上、以点带面,抽绎出有价值的一般规律,实事求是,将艺术学学位论深做实,也应该给予支持。这就是说,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我希望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打消顾虑,消除误解,所有广义艺术与狭义艺术、艺术一般与艺术特殊,都可以进入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视野。而判断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的关键,是看它们的思维指向与方法运用的是不是在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活动规律。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
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
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
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
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
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
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
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
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六、结语
当下,艺术学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有些作者已经写出了由下而上,以艺术门类素材为研究对象,上升到揭示艺术一般规律的论文,却不知道自己在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不自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这种现象并不为怪,就连西方艺术史(狭义的艺术史)研究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论文和论著,甚至某一研究流派。我们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从成立伊始,就一直关注这一现象问题,曾经向东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研究生院(处),征集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目录,刊登于《艺术学研究》上,用“不自觉”的研究可以囊括其中一部分学位论文。但其中也有不少论文还停留在艺术门类的“特殊”研究层面上,并未上升到“艺术一般”。这是历史,无须回避。我们在长期的教学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称此种现象是从不自觉到自觉,逐步形成艺术学理论研究界域的必然发展过程。
篇(4)
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历史”这个词,在我们口里和笔下不知出现过多少遍。但是,我们真的清楚“历史”这个词的意思吗?我们清楚地想过“历史”是什么吗?
什么是历史?
我们常说、常写、常想的“历史”这个词,实际上不止一种意思,但我们常常不大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随手举几个词典上的例子:英文的History,《牛津大词典》有九种解释;中文的“历史”,《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有四种解释;《辞海》和台湾的《中文大词典》、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均有二种,我们不去一一列举了。我们通常的用法中,“历史”一词大致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是指过去的事,第二种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第三种是人们意识中的过去。
(1) 先说第一种,历史是过去的事。
这种用法,例如: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占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不仅限于人类,大至宇宙(现在认为它有120—150亿年),小至基本粒子(10-6—10-23秒),都占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了(个人、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世界)。
雇佣劳动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说的不是一个事件,或事物,而是一种现象,一种关系。
这座房子的历史不长——物体。
医生要了解病人的病史——某个人某些方面的状况。
历史的经验——从人们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认识中总结出来的东西。
总之,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各色各样的事物都在时间中占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地位,在时间已经逝去的那一段,就是它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的事,这是一种简单的直观的表述形式,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最早解释。在中国古代文字中,甲骨文中“史”作“”是象形字,象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和“事” 或不分或略有区别()。史、事相连。甲骨文中有“历”字,作“”,指经历、历法,表示经历的一段时间,下面是一个人脚印,似乎是指人的经历,即今天繁体字的“歷”。历、史连用,事再注入时间观念,成了一个词“历史”,指经过的事。历、史合为一辞,似乎晚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和历史,意思一样,但史的意思更宽一些,还包括了写史的人。甲骨文的史,是人名,是记事的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这个记事者,也是人,即史官、史家。
说历史是过去的事,这是一种简单的直观的表述形式,不错,但并没有完全表述“历史”的内涵。“事”通常被看成是“事件”(event),那是历史中有头有尾,轮廓清楚而且是显眼的东西。但历史中的有些东西不好说是事件,例如关系、现象、心态、过程等等。所以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应该包括了过去的事件、事物(物体现象)、事态(形态、结构、过程)、事情(包括非物质的心理现象)等等。
但是,这样讲也许还不够,尽管历史的“历”已经显示了时间的因素,但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过去的它是什么”,而不一定注意到“过去的它是什么”,即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它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常是从静态的角度如同看照片那样看历史事物,而不是从动态的角度如同看电影那样看历史事物。换言之,历史的事物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活动,而不仅是 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着。因此,我想,比较更确切的提法是:
历史是过去的事物活动的过程。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但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也许更应当说:
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
这里包括了大至社会形态、国家、民族,小至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的无穷无尽的、各色各样的、此起彼落的事件,事物、事态、事情的形成、发展、转换、变化、结束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可以叫做“本来的历史”(历史是不是客观地存在过,是不是仅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就这样认定了,也有人会反对,这里先不去讨论)。说它叫“本来的历史”,那就有“非本来的历史”,下边马上就会讲到。“非本来的历史”与“本来的历史”是相对而言,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处在过去的时间段上,时间是不可停止,也不可逆转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我们无法使它再现(这也是一个问题,历史会不会重演?这到以后再谈)。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那个客观存在过的“本来的历史”已经不再存在了。(这又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过程来说,本来的历史不存在了,但现实生活中、历史的东西还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它不仅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且是我们认识过去历史的一种极重要的资料和手段。这点我们下边再说)。我们必需也只能依据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它的“载体”(不是它本身),或者说,经过一种中介来认识它。这就是有关历史的记述及今天留下来的过去的遗存。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文字记载下来的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写的历史”。这样,我们就有了不是本来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的“非本来的历史”。这是“历史”一词的第二种意思。即:
(2) 历史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
或者说,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的记载。
这种用法,例如:
我们读历史。
我们在上历史课。
这里不是指我们在读那一去不复返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它已不存在了,那是没有法子读的。我们读的是记载那一去不复返的“本来的历史”的历史书。或者是听教师讲那一去不复返的本来的历史的历史课。
又如:
《史记》、《宋史》,信史。
这里指的是某一历史著作,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世人乃至现代人写的。被西方人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他的关于希腊波斯战争的著作就叫《历史》,西汉司马迁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中国通史名字就叫《史记》[2](历史记载)。《孟子·离娄上》:“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即用文字把齐桓晋文之事记载下来,这种对齐桓晋文之事的文字记载就是史,象《春秋》之类。前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书》,“博览书传历史”,这里历史和书传一样,都是“览”的,指的是书,即历史的记载。
在中国,历史和历史记载是一个词,英文也是,都是History。在德文里则是不同的词,称过去发生的事为“Geschichte”(历史),而撰写的历史则为“Historie”(历史记述)。
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就是根据对过去历史的记载来了解那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的。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过去历史的,是通过别人对历史的认识来认识过去的历史的。这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即通过一种载体、中介来认识本来的历史。
说我们是通过历史记载来认识历史,如果仅仅指文字还不够全面、准确,还需要做三点补充。
第一,我们说的历史记载,不仅包括文字,也应包括图象和语言,如口头叙述、录音、图画、照片、电影、电视、光盘、数码等等。
这种历史的记载,除了有目的的以历史为对象的记述外,还应当
包括当时人们并非以传述历史为目的而是应现实生活需要而记录的东西,如档案、帐册、公文、契约、书信、日记,乃至书籍、文章、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有的以原来的实物形式留存下来,有的以传抄、印刷、复制的形式传留下来,这些东西是当时人作的,而不是后人写的,也没有经过后人意识的加工,与专记历史的书不一样。它们在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上,往往超过后来对历史的撰述,即属于所谓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历史记述之外,还有实物,即留存下来的过去的遗物。如遗址、墓葬、建筑、器物等等。这些东西上有些有文字和图象,那就兼具记述和实物两种作用了。留存的历史实物,不是那活着、运动着的过去历史,但可以反映那活着的过去历史的某些东西,也是认识过去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除了上述两类,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通过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历史的东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知识、认识能力、认识方法和认识技术,这些知识、能力、方法和技术是历史地积累形成的。这里先不讲它,以后在讲历史认识论时还要提到。在这里要说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历史的东西,它们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又确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存留、延续和变形,这是我们可以直接接触、认识和体验的。可是,谈认识历史时常常容易忽略了这点,以为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是来自过去历史的东西。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容易讲清楚,我们到讲历史认识论时再说,这里只提一下。
这样,过去历史的“载体”或认识过去的“中介”,就从“写的历史”或“历史记述”扩大到包括过去遗留的实物和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的东西,即把记载的“载”,不仅理解为文字的记述,而含有“载体”的意思。它们都是认识历史的凭借资料,可以说它们都是“史料”。
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的经历,这是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历史,象我们身上的一个伤疤,那就是我们过去历史的实物形式的遗留。这些是对过去的总体历史的很小、极短的一段,这是人们对历史的亲身经历和直接感受,但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而一旦写下来或说出来,对其他人来说,那也就是认识历史的资料即史料了。
史料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本来的历史,甚至不管它是真是假,它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凭借(例如,过去有关于鬼神的记载,并不就能证明鬼神的存在,或过去有鬼神的存在。但这种鬼神记载却可以让我们认识过去人们的信仰、心态、生活,这种信仰、心态、生活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正是通过这种史料,了解那一去不返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形成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这样认识的历史,是主观的东西,意识的东西,也叫“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三种意思。
(3) 人的历史认识,或人所认识的历史。
有位西方学者说:“历史是对过去的回忆。”想来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过去的、本来的历史经过中介(过去历史在今天的各种存留),转移到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即被人所认识:
历史Ⅰ(过去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Ⅱ(史料)历史Ⅲ(人们的历史认识)
这种历史认识,人人都有,人人都需具备,从朦胧的不大自觉的历史意识到具体的、片段的、浅层的历史知识,到系统的历史认识和科学的历史认识。这里面,专门从事历史的记述与研究和从事历史知识的传播的人,又称之为史学工作者,从古代的史官到现在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都是。
中国早在商代就有专门从事历史记述的人,甲骨文的“”字常作人名,往往专指记事的史官。金文中史、事二字分开了,史指史官,事同吏是一个字,记事的官与办事的官分开了。我们把前引的《说文》引全了:“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史是“记事者”,非记事而指记事的人,但又加了一个解释,认为史字象从又持中,“又 ”是手,即手持“中”,中是正,史家要秉“中正”记事,即要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但是,史字是象形字,那个“中”是一个手拿的东西,而“中正”是无形之物,何以能用手持,史字中的 “中”,甲骨文、金文作“”;而中间、中正之中,甲骨文、金文作“”等,与“”显然不是一个字。许慎把“”释成“”,混淆了两个字,而把史字的“中”释成中正之中,显然是后起之义。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清朝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但簿书“中”何以作“”形?吴大徵《说文古籀补》说史“象手执简策形”,简是一根一根的,编简成“册”,甲骨文作,象用绳子把一些简串在一起,和不一样。王国维《释史》说“者盛筭之器也”。筭是算筹,一根一根的,插在一个架子上,就是那个插算筹的架子,这种架子也可以插简,但
上却没有插筹或简,把它释成“盛筭之器”,也还难说。还有人说可能是网罗鸟雀的“畢”,甲骨文作,但也不好说就是如此。总之,那个史字上的字,到底是什么,现在似乎还说不清楚。但史最先是记掌文书的官,他所记载的事也就是史,看来是可以确定的。[3]
在历史记述中,有许多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的产物,象《史记》,那是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述他的历史认识的历史著作。我们常常是通过他们的历史认识去认识历史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司马迁的历史认识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认识过去历史的资料——史料来读。这种历史著作有价值大小高低之分,但其具有历史著作与史料的两重性质则是一样的。
“历史”这个词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例如: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指今天、现在的活动)。
历史将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里的“历史”指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
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里历史的含义已经不仅是过去,而且包括现在和将来了。这是因为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现实,成了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又成了将来的历史,因此也可以把今天和将来纳入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但是,今天的事正在发生,将来的事还没有发生,“历史”还是应该专指过去已经发生的事,而不包括今天和将来。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我们认识的对象,应当是过去的历史,本来的历史。
以历史(过去的、本来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为认识对象(经过中介)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历史科学,即一种知识体系。我们的历史认识可以有四个层次,历史意识——历史知识——历史学(知识体系)——历史科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历史学,不同于某种史学,例如神学历史学)。历史科学的任务是求真,即使我们的历史认识与真实客观的历史一致起来,能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把过去的历史描述出来,使过去的东西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过去的东西是无法还原的,历史学写的历史看来象是还原了,实际上只是也只能是过去历史的一个摹本,一个影象。向来说好的历史是“信史”,“信史”的这个“史”字指的是历史的第二个意思,即写的历史。“信史”这个辞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昭十三年》,指记载真实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可以信得过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和“直笔”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本来的、客观的历史无所谓信与不信,写的历史、所认识的历史则有信与不信之分。信或不信就看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的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与本来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关系是原本与摹本的区别、是原形与影象的区别。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写的历史则是主观的认识。写下来的历史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它是历史学家主观认识的客观存在。一切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一般地说认识充其量也只是相对真理。号称书圣的王羲之写下“兰亭序”,被称作书中极品。但“兰亭序”真本已佚,据说是酷爱此书的唐太宗死时遗言令它陪葬去了。其实早已不知下落。此书唐人摹本很多,最有名的是欧阳询的定武本,此本今已不传,现存有宋代刻石。此外还有神龙本、国学本、冯承素本等。这些摹本虽然近似,临摹者又很认真细致,连款式、删改、纸的折痕、某字落笔时笔锋破了,都很近似。但还是贯注了临摹者独有的书法风格,不能够完全一致起来。写的历史、认识的历史同客观的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主观不断地与客观符合,历史学永远要进步,历史要不断地再写,历史学家也永远有工作可做。这同自然科学一样,而且更有甚之。恩格斯说过“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32页,人民出版社)。我们不妨补充一句,自今而后必须不断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而“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89页,人民出版社)。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历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前提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如果否认这个不可更改的客观历史的存在,或者认为它是可以由主观意识来改变的,那历史学就成为由主观认定而非主客观一致的产物了,曾经说过:实在(我想应该是包括了历史——引者) 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文存》一集卷二,《实验主义》)这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历史学可言了。还有种说法,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个存在却不是我们能认识的,或者说不必要由我们来认识的。既然排除了这个客观对象,那历史就只存在于我们意识中,只有我们意识中的历史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历史学可言了。[4]
还有一种看法,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史料,这是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对认识了的史料作出理解和诠释,这里有对历史理性思想的思维,还要有体验能力,这是非科学和非理性的,需要有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解或精神贯穿其间,还要有史学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些本质上是思维构造过程,受到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制约,因此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是史学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副面貌,然后再经读者去理解诠释,形成读者思想中的历史的面貌,这是历史学的最终结果。
这种说法也很值得讨论。我想,历史确乎需要理解和诠释。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记录,也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和诠释。理解和诠释并非只是“第二层次”的事。认识史料决不只是对史料的搜集记录和排列,同时也需要理解和诠释。问题在于,史学家的理解和诠释应当朝着符合那个客观的历史的方向努力。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那个真实历史。而且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而不是把历史当成自己某种思想的注脚、例子,按自己思想模板去裁剪的衣料,甚或是增加自己思想味道的调料。
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或迟或早总会遇到的问题。虽然有些研究者忽视或回避了它,但它总是在那里。在目前,我们就讲到这个程度。
在这里,我们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它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它的任务是求真。即应当认识和正确反映的是那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历史。
以客观历史为对象,不只作简单的、表层的、现象的描写,“知道了的东西还不因此就是认识了的东西”(黑格尔),还要通过现象、表层发掘其内容中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直接显示出来,只能在史学家思维的运动中才能显示和概括出来,并且要根据客观历史的特点和运动形成一种考察历史的方法。这些就构成了一种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理论”(历史的理论),象历史唯物论,就是这种历史理论(包括方法)。也可以称它为“历史科学理论”或“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的科学理论,这里的“历史” 是指“历史”一词的第一个意思,即客观存在的历史)。它要回答的是客观历史是什么样子,结构如何,运动的规律如何等等。这是一种对客观历史本体的认识,是对历史的内容的认识,或者说,是历史认识的内容,历史的本体论。
历史学或历史科学本身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而是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以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为对象,概括人们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和方法,则是“史学理论”(史学的理论),也可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的理论,这里的“历史”,是指历史一词的第三个意思,即人们的历史认识)。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如何使主观的历史认识同客观历史过程一致起来,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即客观历史的一般形式,为什么要研究它,研究它的什么,历史认识的特点、范畴、原理和规律,如何正确的评价历史,以及如何获得正确认识历史的能力和方法,如何检验历史认识的正确性,等等。它要回答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阐明历史,它不直接研究客观历史,而是研究如何研究历史。“史学理论”不就是历史学,而是“史学学”,如同“科学学”一样。它是历史学的一个方面,它是历史认识论。
现在讲的“史学理论研讨”,就是这样的一门课,它主要讲的是历史认识论。
这门课打算讲五个题目 :
导言 历史是什么。
第一 历史本体论(这里不讲客观历史的具体内容,而是讲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要注意客观历史的哪些方面)。
第二 历史认识论(怎样认识历史)。
第三 历史价值论(怎样评价历史,是历史认识论的延续)。
第四 史学方法论(从历史认识的层次、规律看认识历史的方法)。
第五 历史学的任务和史学工作者的素养(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和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
对这些问题,现在有各色各样的看法,很难说我们这里讲的就是完全正确的东西,毋宁说是提出一堆须要探讨的问题。有些我这里正面肯定的讲法,其实也只是对问题的诸多回答和说明中的 某一种回答或说明。我们这门课的作用,看来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可供大家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把这门课叫做“史学理论研讨”。
那么,讲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它本身既是问题一大堆,并没有能提出明确的、正确的或为大家认同的结论,何况,学它对我们学习研究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涉及它,不也是在研究历史?这倒也是事实,确实许多史学家,也许多数史学家并不搞这些问题,不注意这些问题,也在写论文,写著作,有不少还很有成就乃至有很大的成就 。其实,不弄这些问题不等于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没思考过这些问题不等于脑子里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的甚至非自觉的看法,没有用这些看法来引导、影响自己的研究,没有一个自己的态度。有的人认为这种史学理论问题毫无用处,他的工作就是搜寻史料、排比史料、考证史料,通过史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其实,这就是一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对不对呢,全不全面呢,那就需要考虑了。我想,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态度,有一种看法,可以使我们更自觉地、更正确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学。就象走路,有一个目标,有一种方向或有一种走路的方法,究竟与无目的走路是不一样的。其实无目的走路也是一种方向,一种方法,不过最好还是有一种有目的方向和方法为好。
[1] 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 史记当时是对史书的通称。《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三师涉河。’”司马迁《史记》出,史记始成为专名,这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后成通称,正好相反。
篇(5)
山东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系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单中惠、徐小洲教授主编。选取了10本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由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译者团队,历时5年多精心打造。
本译丛是国内首套翻译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目的在于通过向教育界推介西方教育史经典著作,使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在教育理论素养上有所提高,在教育史学观念上有所感悟,在教育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启迪。
译丛的入选书目体现了三个特色:一是经典性。入选著作在西方教育史学界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具有形成智慧的教育价值。二是代表性。入选著作在西方教育史领域代表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三是独特性。入选著作体现不同的西方教育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国家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其中既有传统史学研究的成果,又有当代史学研究的成果。
教育史蕴藏着教育智慧,教育史经典名著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本译丛将有助于我国教育工作者开阔教育视野和拓宽教育思路,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
各分册介绍: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美]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著 许建美 译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与方法》一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家威廉・W・布里克曼(1913~1986)的代表作,1982年出版。第一版以《教育史研究指南》为书名,于194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在此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进展迅速,但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教育史研究指南》研究范围相似的著作。该书脱销后,从美国、欧洲、南非、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传来重印的要求。于是,布里克曼于1973年将内容拓展后的修订版命名为《教育史研究》,在宾夕法尼亚州诺伍德出版。1982年,他又出版了增加在《教育史》上发表的4篇论文的新版本,并更改为现名。
《希腊的学校》
(Schools of Hellas)
[英]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著 朱镜人 译
《希腊的学校》一书是英国青年学者肯尼思・J・弗里曼(1882~1906)的教育代表作,其副题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代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190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是弗里曼的学士学位论文,也是他为争取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候选人提交的论文。该书研究的是公元前600年至300年之间的古希腊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
《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英]科班(Alan Balfour Cobban)著 周常明 王晓宇 译
《中世纪大学:发展和组织》一书是当代英国知名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大学的知名学者艾伦・鲍尔弗・科班的一本学术专著。1975年出版。该书重点考察大学的历史,诸如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文献、欧洲的学院运动以及中世纪学生权利等。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英]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著 赵卫平 赵花兰 译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1400~1600》和《维多里诺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哈里森・伍德沃德(1855~1929)在西方教育史研究领域、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研究领域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著作。前者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07年(1924年重印),后者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897年。
《教育学史》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法]孔佩雷(Gabriel Compayre)著 张瑜 王强 译
《教育学史》一书是法国教育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孔佩雷(1843~1913)的代表作,副题是“主要教育家及其理论;重要著作分析”。出版于1881年,原书名为《十六世纪以来法国教育理论批评史》两卷本,出版于1879年。1886年,《教育学史》一书由美国著名教育家、密执安大学教授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翻译成英文。
全书除“英文本译者序”和“前言”外,共22章。其特点是:第一,资料丰富且文献详实。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其中包括教育家的著作、教育法令、教育历史事例、教育实践情况等,甚至还有中国老子《道德经》、《犹太法典》以及佛陀与他的弟子的对话。第二,论述简明扼要且分析精辟中矢。该书尽管出版时间较早,但与它以后出版的西方教育史著作相比,它在分析力度和行文流畅上一点也不逊色。尤其是每一章最后面的“分析性总结”,不仅是言简意赅,而且是画龙点睛。第三,凸显法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以被看做是一本法国教育学史。第四,整体论述采取分节的方式。全书的论述共分667节,而且每个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非常清晰明了。
《西方教育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美]伯茨(R. F. Butts)著 王凤玉 译
《西方教育文化史》一书是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R・弗里曼・伯茨(1910~2010)的代表作,其副题为“它的社会和智力基础”。1947年出版。
《教育问题史》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美]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著 单中惠 王强 译
《教育问题史》一书是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巴克(1898~ )的代表作。1947年出版,1966年再版。这是西方教育史学界第一本以问题为研究主线的教育史。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
(Doctrines of the Great Educators)
[英]拉斯克(Robert R. Rusk)、斯科特兰(James Scotland)著 朱镜人 单中惠译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一书是英国教育史学家、乔旦希尔教育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罗伯特・R・拉斯克(1879~1972)与英国教育家和地方戏剧家、阿伯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兰(1917~1983)合著的著作。该书1918年第一次出版,先后一共出过5版。在每一次再版时,作者对内容都作了重新修订,并根据自己认识的变化对人物作了增减。
《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美]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著 单中惠 马晓斌 译
《学校的变革》一书是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阿瑟・克雷明(1925~1990)的代表作。副题为“美国教育中的进步主义”。1961年出版。1964年,该书荣获“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篇(6)
关键词:平行研究;可比性;总体文学
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是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受到质疑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如果望文生义,可以对一切“没有事实关系的跨文化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也就是具有“无限可比性”,那它就“堕入漫无边际的、为比较而比较的滥比,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也就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1}。
的确,“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对应,标志了美国学派不同于法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方法论,这一术语突出了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只注重“文学遗传”的外部事实关系研究的反拨,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鲜明性。然而,“平行研究”这一方法论的提出有具体的话语语境,它有相当丰富的外在表现和实质内涵,绝不是“没有事实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对“平行研究”这一比较文学学科基本概念的梳理、廓清和重新认识,可以使我们对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并切实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避免“乱比瞎比”、“浅层比附”等现象的发生。
那么,“平行研究”这一术语是何人、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提出来的呢·它为什么可以作为美国学派的“标志性”方法流传至今并广为人知呢·
在1958年教堂山会议上宣读的那篇讨伐法国学派的檄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虽然明确反对法国学派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仿照自然科学模式以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学的机械主义,但并未明确提出“平行研究”方法,作者也并未重点强调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之间的“平行”研究。突出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之间的类比关系,明确提出和论证“平行”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是在紧随其后的雷马克的论文《比较文学何去何从:诊断、治疗和予后》中。该文专门考察教堂山会议中两个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本质的大辩论,辟专章重点对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类比”研究的合理性和价值进行了详细探讨。{2}后来,在60、70年代,阿尔德里奇、韦勒克等人在论著中都指出对没有任何关联的作品进行平行的类同比较的必要性。例如,1970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指出:比较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1}
显然,从雷马克明确提出文学之间类比研究的合理性和价值,到美国学派其他学者对平行研究方法的认同,平行研究已经是美国学派公认的方法论基础,这其中与平行研究这一术语极强的包蕴性有直接关系。该术语的提出,围绕着美国学派学者贯穿始终的核心精神和一系列理论主张,有相当丰富的具体表现和本质内涵。
一、平行研究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平行研究的突出表现是“无事实影响关系”。正是围绕着“无事实影响关系”这一核心话题,美国学派的学者展开和发挥了自己的论辩和理论主张。首先,针对法国学派实证性的“史学”特色,美国学派论证和辨析了“无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是否可比”这一问题,从而将文学批评引入文学史研究,构建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维一体”的比较文学理论框架。这样,美国学派将文学作品的“美学性和艺术性”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得以从研究实践上拓展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以“认识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提供一般性解释”为目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实践在时空和知识谱系两个维度得到了拓展:其一,在时空上,平行研究拓展到“无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民族、区域之间的文学研究。例如,时空相距较远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二,在精神和知识谱系上,平行研究拓展到看似“无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知识谱系之间的研究。例如,文学与科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
(一)无事实影响关系的文学是否可比·
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学史”的一支。雄辩而又才华横溢的韦勒克曾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中,通过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名称与实质,深刻地分析了法国比较文学的“史学”特色及其内在缘由。他认为脱胎于19世纪的法国比较文学,其含义是“文学进化的一般理论,即文学要经过产生、成熟、衰亡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因而,法国学派注重研究文学的遗传、渊源和影响等事实关系,在法国学派看来,无事实影响关系的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了文学史的边界,是不可比的。这样,强调实证性、历史性的法国比较文学,就将文学的美学性明确排斥出了比较文学学科,注重文学作品内部的美学评价和分析的文学批评常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推测的”。卡雷在那篇纲领性的《比较文学》序言中,明确指出:文学内部的美学分析(卡雷将之称为影响研究)依靠的是“不可称量的因素”,经常是“靠不住的”。
篇(7)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渊源;黑格尔;约翰・罗斯金;克罗齐
一、黑格尔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关注历史学研究发展,通过追问“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评价与总结史学史中存在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但他并不仅仅通过评述历史学研究证明历史思维方式即“历史地思考”的必要性。他也通过评判西方哲学发展史证明这一论题。在他看来,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的非历史思考方式使哲学研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威胁。而“历史地思考”,是维护哲学研究合法性的重要保障。由此看来,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着力阐明的历史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哲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历史地思考”是人类认识与反思自身文明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当时人文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的越俎代庖现象,即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取代“历史地思考”是柯林武德批判的。
称柯林武德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常”,正是因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系统批判。在此,我们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评述当时西方哲学传统中与柯林武德相关的学者与观点,并不想对其做整体介绍。同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关系一样,这些学者既是柯林武德批判的对象,也是他构建自身理论的学术源泉。从地域上说,西方哲学传统分为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两部分。与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相关的欧陆哲学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黑格尔、意大利的维柯、克罗齐、乔凡尼・金蒂利[1]、吉多・德・鲁吉奥[2]。英国的约翰・罗斯金、史密斯[3]与布莱德雷。这些人物及其观点是以何种方式与柯林武德邂逅的呢?我们可以从学术界对柯林武德的理论定位开始阐明这个问题。
国内学界曾经存在的一种比较广泛的观点是,将柯林武德看作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这典型地体现在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四章“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下)――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中。黑格尔确实是欧陆哲学中对柯林武德理论影响较大的。但是,随着西方历史哲学由思辨的向分析的或批判的转型观点在学界流行,以及注重研究柯林武德在诠释学、美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学术趋向必然弱化学界在历史哲学方面研究柯林武德与黑格尔的关系。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体现在,其划分的三种历史类型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影响了柯林武德的历史思维模式。比较《历史哲学》与《历史的观念》,可以看出柯林武德划定的剪刀加浆糊历史学、鸽子笼式史学、批判的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溯源于黑格尔。“历史学家必须适当考虑他们研究过去的方式,坚持寻求更有效的类别。这种历史有三个阶段,原始的、批判的和哲学的,可能被看做一种形式的等级制。这个等级中的每个形式体现历史的观念,但更高级的形式更全面地体现历史观念。每种形式是特定时段历史观念的体现。每种都被认为最好地表现了历史观念,直到它无效了。当那种无效呈现出来后,历史学家就被迫采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4](P147)“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极有用地表述了柯林武德后来吸收的观点。”[5](P72)在阅读《历史的观念》、《史学原理》过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柯林武德代表性的史学观念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与历史思想的重演均受黑格尔启发。
这种学术承继关系体现在柯林武德对黑格尔“对的”与“错的”评价中。“黑格尔说自然没有历史,因为他完全理解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历史研究首先是历史方法论研究。他认为自己时代的历史方法非常糟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未帮助历史学家完成其职责:它们未能看透记录下来的活动以发现潜存其中的思想。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尽管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历史方法克服了这个困难。”[6](P60)柯林武德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方法是“逻辑强制的”,将历史学置于逻辑学的约束之下,并非真正历史的方法。
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学术立场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二人进行学术思考的环境迥然相异。“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共有三个本质上相似的主张:两人都异常崇拜古希腊人,都独特地拥有其所处时代学术争论的广博学识,都一贯确信人类经验构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如果学者们发现柯林武德的整体性观点不如黑格尔的那么令人满意,那么责任主要在于柯林武德进行研究的氛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牛津是怀疑主义的、专门化的,并非1816年至1831年间充满热情的海德堡与柏林。就柯林武德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达不到黑格尔的高度,而在于在完全相反的工作境况下他的学术观点与黑格尔如此相似。对那些不熟悉黑格尔的人来说,柯林武德的早期著作特别是《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是对这位伟大德国学者的有用导读。”[7](vii)
二、约翰・罗斯金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构建自身史学理论体系,有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批判与超越。“哲学家能够制造外在于历史事件的永恒真理。我们看到了内在于黑格尔世界观中的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使黑格尔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理解。一些人不考虑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用历史资料适应他的哲学观念。另一些人称赞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哲学。然而,两个方面的读者都赞同,黑格尔对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包括历史哲学的影响,使得理解黑格尔说了什么很重要。”[8](P146)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并非通过著作,而是通过柯林武德父亲(威廉・格肖姆・柯林武德)终生忠实追随的哲学家约翰・罗斯金。柯林武德及其姐妹在少年时接受的家庭教育与学术训练内容,都由罗斯金安排。罗斯金经由这种方式将黑格尔及其个人的学术理念传递给柯林武德。
比较两者学术观点的相似性无疑是证明柯林武德与罗斯金之间学术承继关系的理想方法。“更为有趣的是,将柯林武德的演讲《人性与人类历史》与罗斯金的著作比较时,会发现典型的罗斯金式洞察力。柯林武德也认为,无论历史人物何时活动,理解其心中所想是基本的。对他来说,目的比‘偶然事件’(罗斯金)或实际发生事情的‘外部’(柯林武德)更为持久。至于说明柯林武德强调辨明历史当事人思想,他对凯撒穿过卢比康河的阐述,同样可以用来证明罗斯金强调的研究过去活动的目的。”[9](P26)在柯林武德看来,罗斯金虽然主张通过想象重构过去,但是这并非同情式理解即历史地理解。二者差异在于,柯林武德将历史学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理解,并在当下语境中评价。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是历史地理解的关键。
无论如何,罗斯金是柯林武德个人成长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者。柯林武德的广博学识与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主要受罗斯金对生活多侧面研究的激励与启发。罗斯金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在艺术评论、宗教、科学与史学领域著述甚丰,为了能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他甚至放弃稳定工作机会。他不仅活到八十一岁,而且写了几千封信件,坚持写日记并在七十岁时写下个人自传。他强调只有亲自进行艺术实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艺术。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柯林武德在音乐、绘画等领域造诣颇深,也为其后来《艺术原理》写作打下实践基础。两人的丰富著述表明他们都相信书面文字的力量并坚持心灵独立性的理想。与罗斯金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并未放弃而是主动谋求在牛津大学的工作机会。但他始终坚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以致显得与当时学术氛围格格不入。有研究者将他称为其所处时代的“学术孤儿”看来不无道理。
柯林武德为了论证历史知识合法性,一贯坚持历史与自然的区别。虽不能说这种立场完全导源于黑格尔,但与黑格尔紧密相联。“黑格尔主张,在自然领域存在不断的重复,原因与结果彼此相对并外在地联系着。自然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过程,其中发生的现象由外在的必然性促成。在精神领域或心灵领域,所发生的现象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区别于自然中的外在必然性,并且具有创造与发展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倾向。心灵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它能够创造真正的新事物。这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实现完美的强烈愿望。在自然中,由于存在不断的重复,事件是可预见的。在精神领域,过去的逻辑并不能使我们预见未来。”[10](P120)柯林武德继承了这一立场,进一步认为,历史知识是对心灵活动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产生的历史理解模式是一种自律的思想形式。他否定黑格尔将心灵观念作为历史实质的观念,突出认识心灵活动的历史知识,以此论证历史学的合法性。
柯林武德区分、探讨历史学的先验概念(作为一种活动形式)与经验概念(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之后,指出历史哲学研究的指向是历史学的先验概念。历史学的这种先验概念是无需定义、一看便知的。他的这种观点彰显他与黑格尔的相似之处。黑格尔声明其历史哲学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历史学概念的哲学思考。这是在研究柯林武德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克罗齐与柯林武德
为了更清楚说明柯林武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国内学界曾将柯林武德作为克罗齐后学,并分析比较二者观点相似性以证明这种师承关系。柯林武德《自传》对此却惜墨如金,并未表露意大利的影响,因此遭到指责。这种状况与学界直接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思想挂钩,却未关注这种学术影响发生的方式有关。柯林武德导师卡里特在“哲学家茶座”上结识史密斯,史密斯向柯林武德介绍克罗齐的著作,并在1923年向克罗齐推荐柯林武德。史密斯本人也是克罗齐学说的信奉者。柯林武德在此过程中陆续翻译了克罗齐的《维柯的哲学》、《自传》和《美学》。克罗齐影响柯林武德另外一种、也是更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其两个学生乔瓦尼・金蒂利和吉多・德・鲁吉奥。在与史密斯及克罗齐两个学生的学术往来中,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中历史化的特点很感兴趣。经过柯林武德自己的探索,“历史化”也成为其学说特点。
柯林武德面对的两种英国哲学传统是实在论与格林学派的唯心主义。继承格林学派精神衣钵的柯林武德,认为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当时学术界属于“小众”,甚至也像实在论一样出现衰落迹象,面临崛起的重任。在寻求解救方法过程中,他遇到欧陆哲学中的克罗齐及其两个学生的学说。在与霍华德・汉内共同英译鲁吉奥《现代哲学》的“译者前言”中,柯林武德写道“这部著作的首要特点也是意大利唯心主义的基础是,最为彻底的历史训练。唯心主义对这些意大利学者来说,正如对黑格尔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哲学。”[11](P6)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历史化”是由克罗齐开启的意大利哲学的新发展,也是他找到的摆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危机的“夷之长技”。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发展最清晰地体现在自由的发展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阐述的自由发展过程,典型体现了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逻辑。克罗齐认为,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就是这种关于对立面关系的辩证法观念。“哲学概念不是从一个种及其从属方面界定。哲学概念内部包含彼此相异的形式,它们与其他形式及整体联合。”[12](P82)但克罗齐并不赞同黑格尔下述观念。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概念是正―反―和。这就要求彼此相异的对立面在一个新的概念中统一。正如彼此不同的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在更高级的哲学的历史学中得到统一一样。而克罗齐认为,和即正反,即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学内部彼此有差异的构成要素,两者的统一不需要一个更高级的第三者,这种统一是一种内在的统一。跟随克罗齐,柯林武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早期柯林武德将哲学,后期柯林武德将历史学分别作为其在《精神镜像》中阐述的五种经验形式最终统一的归宿。
按照大卫・布歇的观点,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克罗齐的学术影响“讳莫如深”是因为这种影响太过明显而无需言说。但柯林武德却坦承另外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他的影响。“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学理论是第一个确切地阐明强调过去与现在差异,强调历史学家同情地理解过去的必要性,并拒绝笛卡尔要求的缜密证明。”[13](P76)否定了笛卡尔的历史知识怀疑论,维柯的历史知识论立场也为柯林武德继承下来。“柯林武德辨别历史学与哲学关系的信念,是维柯175年前在新科学这一标题下创始的方法。……失去的科学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反思的。”[14](P95)从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上证明历史知识的合法性与独特性,是柯林武德孜孜以求的。
柯林武德对克罗齐的影响表面上闪烁其词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他的学术经历中,并未与克罗齐本人而是与克罗齐的两个学生金蒂利和鲁吉奥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学术联系。这在其学术著作和书信中都有体现。超越心物二分法,强调哲学的历史特点这些学术主张主要是柯林武德从金蒂利和鲁吉奥那里习得的,也对他个人学术创造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在史学理论方面,笔者认为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的学缘关系界定为因学术观点相似而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朋友”关系,比“师徒”关系更为恰当。“重要差别在于,坚持克罗齐影响了柯林武德不如比较二者著作意义深刻。尽管柯林武德可能从克罗齐、维柯和金蒂利那里借用了大量术语。但他的灵感来自他处。已有足够证据表明,约翰・罗斯金是柯林武德目标与灵感的主要来源。柯林武德用意大利学者的哲学术语准确表述了罗斯金灌输给他以范例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柯林武德对克罗齐表达了极大同情,然而让人感觉他并非这位意大利人学徒的原因。”[15](P68)二者不同的研究领域可以证明这一点。克罗齐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学、文学评论和现代欧洲政治史。而柯林武德主要致力于考古学、罗马不列颠古代史、哲学和艺术研究。即使如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克罗齐影响了早期柯林武德思想。“柯林武德尤其赞同克罗齐的一点是,通过将历史学与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比较,才能最充分地描述历史学。这就是柯林武德在《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中试图论证的。那本著作在一些方面延续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柯林武德做了很多修改,将宗教提升为一种经验模式,将经济学与道德降级。然而,如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哲学年鉴上查找在柯林武德之前描述经验模式的哲学家,克罗齐赫然耸现。可以确定的是,金蒂利在克罗齐论题上做了一些修改,并为柯林武德吸取。黑格尔是这项研究的学术来源。但正是克罗齐在二十世纪重新使用这种方法,那也是他对早期柯林武德最重要的贡献。”[16](P76)
史密斯以的方式将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历史哲学介绍给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就职演讲《美学与实践》内容就是意大利思想。柯林武德也是受众之一,他所热衷的历史化方法即由此获得灵感。“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特点是历史的。……史密斯直接被意大利唯心主义的这个方面吸引,而且查明维柯在其表达方面的影响。史密斯强调,这些意大利学者突出历史学在塑造哲学上的作用并将哲学作用规定为‘理解历史,首先是哲学自身的历史’。……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柯林武德发现这些意大利人与他是意气相投的,与他个人的哲学倾向是协调一致的。如果柯林武德的《自传》可以信赖的话,他在牛津学习哲学史上重要人物时期,独立地了解了意大利哲学。这段时期就是史密斯提高他意大利语水平,以使他更彻底更准确地理解意大利思想家的时期。”[17](P14)史密斯对意大利学者的热切关注对柯林武德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柯林武德对史密斯的学术影响并未表现出写作《自传》时号称坚持的秉笔直书原则。
柯林武德对史密斯影响的评价不客观,认为他是个失败者,“未能避免自己所属学派(按:指格林学派或唯心主义)瓦解的命运”,不承认带领自己接触意大利哲学的这位引路人的启蒙教化之功。“他们(指史密斯和乔基姆)不能写作,因为感觉没什么可写”。[18](P18)虽然柯林武德在《自传》中直接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重,但这种评价仍带有蔑视和人身攻击的味道,使得本应客观的学术评价变了味儿。柯林武德本人也未逃脱“躺枪”的命运,后来也成为这种评价的对象。亚瑟・马维克在评价柯林武德时更有“谩骂”的味道。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对海登・怀特的评价也充满火药味。或许这就是西方学者学术评价中的常态,笔者认为这也是其人情味儿的体现。
对于布莱德雷,柯林武德将其视为超越的对象,根本没有谈及布莱德雷对他的影响。这同样是不公正的。1914年,柯林武德在莫顿结识当时正在撰写研究布莱德雷论文的艾略特。“1932年,柯林武德第一次得到他和艾略特无比敬重的形而上学家布莱德雷的鲜为人知的著作。这就是1874年首次出版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这也成为柯林武德关键艺术术语的来源。”[19](P215)柯林武德的学术风格明显受布莱德雷影响。
从学术谱系上说,柯林武德的思考方式是承袭黑格尔的,对其历史学思考的最大影响者是维柯,对其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者是克罗齐。如果我们在柯林武德著作中按图索骥,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历史思想家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直接的、隐蔽的,这种关系并不是直线的、即时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用这些原则审视柯林武德对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的研究,我们发现柯林武德对不同思想家做了不同解释。但他是在详尽阐述那些使他感兴趣观念的过程中被它们吸引,进而研究它们的。我们已经理解柯林武德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实践兴趣源于他的少年时代。看来好像柯林武德在意大利唯心主义者中发现了一种从哲学方面讨论他从其父亲那里吸收的多方面兴趣。正是柯林武德兴趣的多样性和对多个学术领域的掌控能力,使他‘能够取经’于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正是柯林武德几乎独一无二的心智上的多才多艺,‘使他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正是这种多才多艺使柯林武德运用他们的文化哲学结出累累硕果。”[20](P89)柯林武德对这些学术前辈的文本或理论主张不是单纯阐释性的介绍,而是创造性的运用。
不同于戏剧,真实生活本身是不能排练的。但在人一生的跌宕起伏展露出来后,体现出来的连贯性及时间本身赋予它的线性发展似乎又表明其中存在着刻意的规划。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成长阶段都存在不同促动因素,而个人思想发展也会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因而,用某种单一的“因―果”模式,去解释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轨迹或思想发展轨迹是不客观的。柯林武德一生的思想发展就展现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体系,是上述任何一个影响来源都不能解释的。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努力与学术原创性,而且对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对实在论的反抗、对历史学发展状况的自觉关注与理论辩护,只有在柯林武德的学术问答体系中才真正成为与历史知识性质相关的问题。结合英国学术境况批判性地引入欧陆哲学传统,针对英国学界问题批判占据哲学主流的实在论并修正英国唯心主义传统,使柯林武德成为一位地道的学术“反叛者”。但这个反叛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留有既往思想传统的痕迹。
参考文献:
[1]全名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学术观点与克罗齐有相合之处,政治观点与克罗齐向左,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
[2]全名Guido de Ruggiero,意大利哲学史家,赞同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唯心主义学说,先后在墨西拿大学和罗马大学任教。
[3]全名John Alexander Smith,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牛津大学道德与形而上学哲学教授。
[4][8]Marnie Hughes-Warrington,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M],New York: Taylor &Francis Group,Routledge,2008.
[5][10][12][17]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6]R. 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 Dusse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9][15][16][20]William M. Johnston,The Formative Years of R.G.Collingwood[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7.
[11]Guido De Ruggiero,Modern Philosophy[M],transl. by A.Howard.Hannay & R.G.Collingwood,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1.
[13][14][19]Fred Inglis,History Man: 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8]R. G. 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